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跨學(xué)科聯(lián)合調(diào)查的實(shí)驗(yàn)與求解
時(shí)間:2020年09月12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shù):
摘要:文化遺產(chǎn)及其保護(hù)作為人類知識(shí)體系的一部分,對(duì)知識(shí)的關(guān)聯(lián)性提出很高要求,因此具有以跨學(xué)科形式開展研究的必要與合理性。 但由于學(xué)科間“不可通約性”的存在,各學(xué)科會(huì)在各自研究范式內(nèi)推進(jìn)工作,難以跨學(xué)科交融形成合力。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組織的具 有跨學(xué)科性質(zhì)的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聯(lián)合工作坊案例顯示,公共空間可以成為各學(xué)科開展研究的具體問題交集,由此可知:在具體的文化遺產(chǎn)跨 學(xué)科研究中,應(yīng)當(dāng)協(xié)調(diào)多學(xué)科間的合作模式,以問題牽引方法求得交集;同時(shí),應(yīng)注重學(xué)科方法在時(shí)間維度上、在全局和個(gè)體尺度上的延 伸交融,求得并集。
關(guān)鍵詞:文化遺產(chǎn);跨學(xué)科;鄉(xiāng)村遺產(chǎn);公共空間;遺產(chǎn)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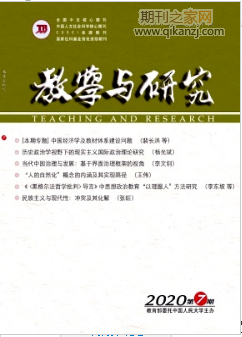
一、“合”的必要:作為跨學(xué)科研究的 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
回溯人類知識(shí)體系,對(duì)知識(shí)進(jìn)行劃分并建構(gòu)體系在 西方古典時(shí)期已出現(xiàn)。基于存在的世界,人類以各不相 同的、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描述的 “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 ways)”的自然觀來觀 察解釋,也因此誕生不同學(xué)科[1]。
自古希臘哲學(xué)家起,便開始嘗試對(duì)知識(shí)分類,如亞里士多德將知識(shí)分為理論哲 學(xué)、實(shí)踐哲學(xué)、創(chuàng)造哲學(xué)三類。中世紀(jì)時(shí)期的歐洲,牛 津大學(xué)、巴黎大學(xué)等古老學(xué)府設(shè)置文學(xué)、法學(xué)、神學(xué)、 醫(yī)學(xué)等課程,傳授較此后更為綜合的知識(shí)[2]。 文藝復(fù)興至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認(rèn)知與生產(chǎn)力均有 巨大提升,在古典知識(shí)基礎(chǔ)上建立了成百上千的門類科 學(xué)。19世紀(jì)上半葉,隨著學(xué)科分化,現(xiàn)代學(xué)科逐步成 型,知識(shí)體系愈加精細(xì)專門化。
此時(shí),培根(Francis Bacon)、孔德(Auguste Comte)、杜威(Melvil Dewey)等對(duì)學(xué)科從不同切入點(diǎn)進(jìn)行分類,如杜威創(chuàng)造 十進(jìn)分類法(DC法),將知識(shí)分為10大類,各大類下進(jìn) 行二級(jí)劃分,對(duì)現(xiàn)代圖書館管理影響深遠(yuǎn)[3]。不斷細(xì)致的 學(xué)科劃分符合彼時(shí)資本主義的轉(zhuǎn)型:從粗放型資本積累 轉(zhuǎn)向密集型資本積累,這一轉(zhuǎn)型過程伴隨著不斷的勞動(dòng) 分工與再分工,對(duì)事物不斷切分細(xì)化,集中表現(xiàn)于20世 紀(jì)30—50年代誕生于美國的福特主義,之后擴(kuò)散至全球 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家[4]。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一 段描述強(qiáng)烈展現(xiàn)出彼時(shí)學(xué)科中的分工特征:“科學(xué)已經(jīng) 進(jìn)入一個(gè)先前所不知道的專業(yè)化階段……個(gè)人只有在他 是一位嚴(yán)謹(jǐn)?shù)膶<业膱龊希拍茉诳茖W(xué)領(lǐng)域獲得某種關(guān) 于真正完滿的東西的確定意識(shí)”[5]。 但20世紀(jì)末以降,正如1970年代福特主義由于內(nèi) 在缺陷與外部條件變化帶來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一般,走向 極度不可通約的學(xué)科分化與未來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全球化、豐 富化的聯(lián)接轉(zhuǎn)換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指出“流動(dòng)性”成為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最大 特征①,流動(dòng)突破相對(duì)靜止的狀態(tài)和與之適應(yīng)的觀念及評(píng)價(jià)原則,這股強(qiáng)大的力量對(duì)原有狀態(tài)提出多方面的嚴(yán) 峻挑戰(zhàn)。
人們不得不尋求交融之路,“跨學(xué)科”一詞也 逐步出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各類跨學(xué)科研究的涌現(xiàn)展示出 其時(shí)代的必要性,表現(xiàn)于二戰(zhàn)后西方不斷出現(xiàn)的新興研 究領(lǐng)域,如生命科學(xué)、環(huán)境科學(xué)等。 卡斯特同時(shí)指出,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到來會(huì)喚起社會(huì)成員 自主建構(gòu)一種集體認(rèn)同,一種對(duì)全球化趨同的抵抗性認(rèn) 同:“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認(rèn)同 的對(duì)立趨勢所塑造”,“這些集體認(rèn)同為了捍衛(wèi)文化的 特殊性,為了保衛(wèi)人們對(duì)自己的生活和環(huán)境加以控制, 而對(duì)全球和世界主義提出了挑戰(zhàn)”[6]。 對(duì)趨同的抵抗、對(duì)集體認(rèn)同的建構(gòu),生發(fā)出現(xiàn)代的 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運(yùn)動(dòng)。
可見,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作為人類知識(shí)體系的一部分, 未來為應(yīng)對(duì)更廣泛且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問題,具有跨學(xué)科研究 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特別地,以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全球化、城 市化帶來的抵抗性集體認(rèn)同又強(qiáng)化了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 在未來的重要性;鄉(xiāng)村遺產(chǎn)本身的系統(tǒng)性以及構(gòu)成特征 使其在跨學(xué)科研究上更具必要性。國內(nèi)的鄉(xiāng)村遺產(chǎn)研究 和實(shí)踐經(jīng)過近20年的發(fā)展,對(duì)跨學(xué)科研究必要性的認(rèn)識(shí) 逐漸清晰。
截至2019年6月,我國相關(guān)主管部門已陸續(xù)公布了 五批共6819個(gè)中國傳統(tǒng)村落。國家有關(guān)管理部門、學(xué) 術(shù)界以及各相關(guān)實(shí)踐領(lǐng)域在20年間經(jīng)過對(duì)文物保護(hù)單 位、世界文化遺產(chǎn)、歷史文化名村、美麗鄉(xiāng)村建設(shè)、中 國傳統(tǒng)村落等與鄉(xiāng)村相關(guān)的不同系列的探索與積累,已 經(jīng)在調(diào)查、規(guī)劃、建設(shè)、登錄管理等層面形成了相對(duì)穩(wěn) 定、各有側(cè)重的工作方法和研究范式。
例如:以孫華 (2015)的一系列文章[7-9]為代表,反映了其團(tuán)隊(duì)基于 西南民族村落調(diào)查與保護(hù)研究的十年積累,實(shí)際上已經(jīng) 對(duì)傳統(tǒng)村落采取了一定的跨學(xué)科方法,形成了認(rèn)知理 論;在管理與實(shí)踐領(lǐng)域,相應(yīng)的一套標(biāo)準(zhǔn)流程經(jīng)由《傳 統(tǒng)村落評(píng)價(jià)認(rèn)定指標(biāo)體系(試行)》[10]、《傳統(tǒng)村落保 護(hù)發(fā)展規(guī)劃編制基本要求(試行)》[11]、國家標(biāo)準(zhǔn)《傳統(tǒng)村落保護(hù)與利用(征求意見稿)》②等文件,形成了 一套可資參照的技術(shù)規(guī)范和操作指南,其中已經(jīng)開始吸 收社會(huì)調(diào)查、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方面的內(nèi)容。
羅 德胤(2017)[12]、杜曉帆團(tuán)隊(duì)(2018、2019)[13-15]等 近年的村落保護(hù)研究和實(shí)踐體現(xiàn)了建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文 化遺產(chǎn)學(xué)等多學(xué)科融合的方法與行動(dòng);地理學(xué)者的研究 則從系統(tǒng)論出發(fā),構(gòu)建了鄉(xiāng)村人地關(guān)系地域系統(tǒng),將鄉(xiāng) 村保護(hù)與發(fā)展相關(guān)的各個(gè)學(xué)科均納入其中[16];文化遺產(chǎn) 與旅游的融合發(fā)展從政府機(jī)構(gòu)改革層面到理論與實(shí)踐均 是近年備受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之一,兩領(lǐng)域?qū)W者通過聯(lián)合工作 坊、筆談等形式進(jìn)行對(duì)話和討論[17-19]。
然而,雖然在學(xué)術(shù)層面和國家管理層面對(duì)于傳統(tǒng)村 落的保護(hù)與發(fā)展形成了多學(xué)科融合的觀念,但在實(shí)踐領(lǐng) 域,即便要求開展社會(huì)調(diào)查、“非遺”登記等工作,傳 統(tǒng)村落保護(hù)規(guī)劃仍然更多地按照工程項(xiàng)目來管理,沿用 著規(guī)劃、設(shè)計(jì)工程的話語體系和執(zhí)行標(biāo)準(zhǔn);相應(yīng)地,遺 產(chǎn)保護(hù)教育層面雖然已開始探索,但與教學(xué)體系上形成 公認(rèn)可行的鄉(xiāng)村遺產(chǎn)調(diào)查研究多學(xué)科融合或交叉的教學(xué) 方法尚有較大距離。
那么,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究竟如何以跨學(xué)科的方式 來研究并實(shí)踐?在“不可通約性”尚存的狀況下,各學(xué) 科如何關(guān)聯(lián)并協(xié)調(diào)? 有鑒于此,2019年“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聯(lián)合工作坊” 北京大學(xué)暑期課程組建了集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考古、建 筑、旅游、社會(huì)學(xué)、規(guī)劃、景觀、藝術(shù)、傳媒等多學(xué)科 師生組成的聯(lián)合團(tuán)隊(duì),前往山西省平遙縣的東戈山村和 西戈山村進(jìn)行調(diào)研③。這是一次文化遺產(chǎn)多學(xué)科聯(lián)合調(diào) 查與教學(xué)的探索,以調(diào)查報(bào)告、發(fā)展建議、藝術(shù)創(chuàng)作、 展覽呈現(xiàn)為成果,嘗試了對(duì)鄉(xiāng)村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開展跨學(xué) 科聯(lián)合調(diào)查的研究與教學(xué)實(shí)驗(yàn)④。
二、求交集:以共同問題牽引方法 平遙縣處于太原盆地的西南,整體地形東南方倚太岳山北麓,山勢由東南向西北順勢而下,西北部成為汾 河河谷,其地形地貌可劃分為平原區(qū)、臺(tái)地區(qū)、山地 區(qū)三個(gè)部分。東戈山、西戈山村位于平遙縣東南,距離平遙縣城直線距離約11.5千米,乘車抵達(dá)約 需50分鐘。兩村緊鄰,通過鄉(xiāng)道與東泉鎮(zhèn)連接。東、 西戈山村處于溝壑交錯(cuò)的臺(tái)地區(qū),全村占地面積分別約 3225畝與3083畝,東西兩側(cè)被自然沖溝所夾,與周邊 農(nóng)田一道形成自然質(zhì)樸的黃土丘陵鄉(xiāng)村景觀。
東、西戈山村緊鄰河谷而建,所鄰河谷過去可能曾 經(jīng)是匯入惠濟(jì)河的支流,如今已經(jīng)干涸。村莊依地形 分布,內(nèi)有防御性的古堡,有堡墻、堡門等防御性設(shè)施遺存,村內(nèi)建筑布局較為規(guī)整。從1968年美 國拍攝的衛(wèi)星地圖上還能看到明清遺留的村落 格局。與今日的衛(wèi)星地圖對(duì)比,可以 看到東、西戈山村舊村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格局 特征,在西戈山村以東和東戈山村以北及以南 部分地區(qū)建設(shè)了新村。
兩村在歷史上 都是典型的農(nóng)業(yè)村莊,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發(fā)展較為 薄弱。東戈山居民以王姓為主,西戈山以裴姓 為主,兩個(gè)家族歷史上均從事過商業(yè)與醫(yī)藥行 業(yè),誕生過在晉中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 兩村建筑肌理規(guī)整,傳統(tǒng)的木構(gòu)、土墻、 土窯、錮窯、土堡組成了建筑語言的基底,村 中保存有少量風(fēng)貌較好的古建筑、民居大院, 例如東戈山的寶禪寺、王治臣宅院,西戈山的 三官廟、裴氏祠堂、敬業(yè)庵等,雖然不乏明清 時(shí)期原構(gòu)和精美雕刻,但以文物建筑的眼光來 看,其年代、結(jié)構(gòu)、形制、成片規(guī)模方面并無 稀缺性。村中夾雜著荒頹、破敗的民居古寺, 老村邊緣以及新老村交接地帶填充著新建的磚房。
這樣的景觀在華北地區(qū)的傳統(tǒng)村落 中比比皆是,具有比較普遍的代表性,卻絕非 “突出”⑤。研究目標(biāo)在于對(duì)兩個(gè)村進(jìn)行初步的 田野調(diào)查,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現(xiàn)問題,并為未來制定一個(gè)初 步的保護(hù)發(fā)展建議。 工作坊分為古建筑、規(guī)劃、旅游、社會(huì)、藝術(shù)五個(gè) 組開展調(diào)查研究。初步任務(wù)以學(xué)科內(nèi)常規(guī)工作為主,如 訪談?wù){(diào)查、村落空間描繪、典型歷史建筑測繪、旅游資 源評(píng)估、重要節(jié)點(diǎn)設(shè)計(jì)、藝術(shù)采風(fēng)等,分別取得了一定 的基礎(chǔ)性成果。但關(guān)于五組的成果如何跨學(xué)科交融形成 合力,起初并未找到方法,成為影響工作推進(jìn)的急迫 問題。
三、求并集:歷史與未來、全局與個(gè)體
為歷史研究加入社會(huì)的視角、為社會(huì)研究加入時(shí)間 的維度,亦是一種跨學(xué)科方法的聯(lián)合。 趙世瑜關(guān)于“大歷史”與“小歷史”的區(qū)域社會(huì)史 研究范式[23],李軍關(guān)于“小共同體”向“大共同體”擴(kuò) 散的遺產(chǎn)化過程論述[24],均提示我們應(yīng)當(dāng)反復(fù)以不同尺 度來關(guān)注村落——一個(gè)村落既是中國社會(huì)某一區(qū)域的細(xì) 胞,又是一群人基于地緣、親緣結(jié)成的社區(qū)。是人們在 土地上的日常生活,造就出今天所見的鄉(xiāng)村遺產(chǎn)。
從區(qū)域的層面,關(guān)于華北鄉(xiāng)村常見的關(guān)鍵詞常包 括:人口流動(dòng)、城鄉(xiāng)聯(lián)系、商業(yè)發(fā)展、水案糾紛、祈雨 儀式等,具體到平遙鄉(xiāng)村,還集中呈現(xiàn)出在清末具有代 表性意義的“代管村落”現(xiàn)象⑥,反映了社會(huì)史家關(guān)注 的“國家的在場”“基層治理”等相關(guān)問題。將上述歷 史上的村際活動(dòng)置于地域系統(tǒng)中考察,有助于理解鄉(xiāng)村社會(huì)活動(dòng)給歷史上的城鄉(xiāng)體系、村落空間留 下的諸多建成遺產(chǎn)印記的形成過程,并獲得 全局性的認(rèn)知。
時(shí)間維度的加入使我們對(duì)于村落過去與 現(xiàn)在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系有了認(rèn)識(shí)的可能。社會(huì)史 家已指出1950年代以來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集體化、 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等一系列變化反映出的對(duì)于 水利公共資源使用的問題和應(yīng)對(duì), 其實(shí)在歷史上就有鏡鑒[25]。水作為公共資 源,歷史上產(chǎn)權(quán)一直不清晰,圍繞其產(chǎn)生過 各種斗爭、制度和經(jīng)驗(yàn)。這些歷史經(jīng)驗(yàn)有些 可資當(dāng)今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治理借鑒、預(yù)判,有些則至少能幫助我們理解在地社區(qū)集體和個(gè)體的價(jià)值趨向與認(rèn)知結(jié)構(gòu)的源流。
如果說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調(diào)查研究在時(shí)間軸上 向過去看可以成為區(qū)域的社會(huì)史研究或村落 與集體的記憶研究,成為我們理解當(dāng)下的基 礎(chǔ);那么向未來看,則為我們規(guī)劃和傳續(xù)傳 統(tǒng)村落遺產(chǎn)提供了方法和反思的途徑—— “情景規(guī)劃”的運(yùn)用,是本次工作坊在未來 這一向度上的研究嘗試。 情景規(guī)劃(Scenario Planning)以描述 性的語言,帶入典型化的個(gè)人角色,通過對(duì) 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地未來極端情況下的狀態(tài)進(jìn)行 猜想,發(fā)現(xiàn)其潛在的影響大且不可預(yù)測的問 題,從而提前提出解決對(duì)策,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⑦。
它既要求掌控全局的意識(shí),從而合理設(shè)置出 極化場景,又落實(shí)在個(gè)人化的表述形式上。 雖然是以模型形式作出極化假設(shè)和情景設(shè) 想,但其創(chuàng)造性、細(xì)節(jié)性、社區(qū)性的特點(diǎn), 實(shí)則建立了規(guī)劃制定者與當(dāng)?shù)厣鐓^(qū)的共情聯(lián)系,增強(qiáng)了 代入感。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定量與質(zhì)性研究的氣質(zhì)平行,它 的想象力和共情性顯示出人文關(guān)懷。工作坊成員基于情 景規(guī)劃,反推出村落社會(huì)保護(hù)與發(fā)展的威脅,例如學(xué)校 搬遷、人口外流的負(fù)向循環(huán)機(jī)制,旅游業(yè)對(duì)村落影響的不確定性等。
由上可見,如果將“全局—個(gè)體”“過去—未來” 視為兩軸來建立坐標(biāo)系,可以獲得關(guān)于個(gè)體的歷史、全局的歷史、個(gè)體的未來、全局的未來四個(gè)象限,涉及的 學(xué)科至少包括社會(huì)史(歷史)、社會(huì)學(xué)及規(guī)劃學(xué)。跨學(xué) 科方法在這兩個(gè)維度延展以獲得的并集,對(duì)于更大范圍 引起共情具有有效作用。
四、結(jié)語
當(dāng)城市被全球化帶來的大量同質(zhì)化符號(hào)及去地方化 建設(shè)充斥時(shí),鄉(xiāng)村更成為承載地方文化傳統(tǒng)與多樣性的 物質(zhì)空間。藉由一次跨學(xué)科的實(shí)驗(yàn)研究,可以看出, 在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帶來日益全球化、同質(zhì)化的社會(huì)形態(tài)中,文 化遺產(chǎn)保護(hù)是自發(fā)性集體認(rèn)同的一種表現(xiàn),因此它不僅 僅是針對(duì)某一地區(qū)的本土化問題,更是廣泛性的世界問 題,本身對(duì)知識(shí)的關(guān)聯(lián)性就提出極高的要求。
正如孫華所言:“傳統(tǒng)村落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系統(tǒng),保護(hù)傳統(tǒng)村落并使村落保持發(fā)展的活力,自然也是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研究傳統(tǒng)村落更需要跨學(xué)科的合作,而跨學(xué)科需要補(bǔ)充通識(shí),擴(kuò)大公約數(shù),才能讓各學(xué)科的成 員們有貫通對(duì)話的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以問題牽引求交集,從歷史與未來、全局與個(gè)體兩個(gè)維度求并集,以求得關(guān)聯(lián)和整合。
教學(xué)論文投稿刊物:《教學(xué)與研究》(教研版)辦刊宗旨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xué)與研究服務(wù),同時(shí)發(fā)表相關(guān)的教育教學(xué)研究成果。為推動(dòng)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xué)與研究發(fā)揮了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好評(píng)。《教學(xué)與研究》(教研版)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及中國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核心期刊。讀者對(duì)象是高校、各級(jí)黨校、各類成人院校的理論課教師,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工作者,以及廣大一線中小學(xué)、幼兒園各學(xué)科教師。
人類的整體知識(shí)從分化走向整合,但這種整合不是簡單地恢復(fù)過去、否認(rèn)已有的學(xué)科分類、讓人人成為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那樣的“英雄”,而是站在人類已有生產(chǎn)力提升、勞動(dòng)分工的基礎(chǔ)上,應(yīng)對(duì)未來廣泛問題的一次關(guān)聯(lián)整合。在具體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研究與實(shí)踐中,基本問題在于如何將與其相關(guān)的多種學(xué)科有效協(xié)同,真正意義上突破多學(xué)科協(xié)同時(shí)的不可通約性。
參考文獻(xiàn):
[1][22](美)托馬斯·庫恩.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M].金吾倫,譯.北 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
[2] 金吾倫.跨學(xué)科研究引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41–46.
[3] 劉仲林.現(xiàn)代交叉學(xué)科[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1–54.
[4] 謝富勝,黃蕾.福特主義、新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兼論當(dāng) 代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家生產(chǎn)方式的演變[J].教學(xué)與研究,2005(8).
[5](德)馬克斯·韋伯.社會(huì)科學(xué)方法論[M].楊富斌,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7.
作者:張劍葳、杜林東
-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背景下基層財(cái)務(wù)審計(jì)的困境與對(duì)策
- 鄉(xiāng)村教師形象的問題審視及其重構(gòu)
- 新媒體背景下如何將環(huán)境保護(hù)意識(shí)滲透到高中生物教學(xué)中
- 漳鹽文化在漳縣職業(yè)學(xué)校的保護(hù)與傳承研究
- 打造科研型鄉(xiāng)村教師“聽說讀寫做”工作模式探究
- 學(xué)校組織文化如何影響鄉(xiāng)村青年教師留崗意愿
- 淺談環(huán)境保護(hù)與化學(xué)教學(xué)中的關(guān)系
- 鄉(xiāng)村小學(xué)生誠信觀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 教育公平視域下鄉(xiāng)村幼兒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困境與發(fā)展模式選擇探究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fù)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fù)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yī)學(xué)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yè)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qū)和影響
- 2025-02-10經(jīng)管專業(yè)快速發(fā)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huì)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huì)議在哪發(fā)論文,解答及指導(dǎo)
- 2025-03-01EI會(huì)議論文值得發(fā)嗎?2025EI會(huì)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shù)據(jù)庫?scopus數(shù)據(jù)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píng)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shí)
- 2025-04-01復(fù)合材料科學(xué)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jí)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jié)能領(lǐng)域論文選題31個(gè),
- 2025-03-28電子技術(shù)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xiàn)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fā)表的論文文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