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英國工業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時間:2019年09月03日 分類:科學技術論文 次數:
摘要: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大量新資料的出現與整理、經濟學研究方法在史學界的運用以及對舊史學思潮的批判,學者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產生了新的范式。不同于以往的“樂觀派”與“悲觀派”,新范式的領導者們經過對“工業革命”這個概念的艱深探索,認可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發展,但又認為這時的發展非常緩慢。新范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使用檔案的先天不足,研究者本身的思維漏洞,研究方法單一等問題,仍然值得后來的研究者警惕與反思。
關鍵詞:英國;工業革命;新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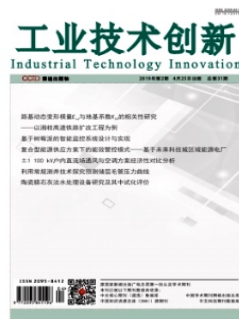
1962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科技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其新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中,對其在1959年便已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進行了諸多發揮。雖然仍然沒有對這一概念給予一個清晰的定位,但庫恩的大體意思是清晰的“:范式”就是科技史上某些重大的科技成就所形成的某些內在機制和外部社會條件,是一種先于具體科學研究的核心構架。對庫恩來說,科學史上的所謂革命性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種核心構架,即范式轉移(Paradigmshift)。[1]后來,這種“范式”概念雖然飽受爭議以至于庫恩本人都避免使用,但它的影響卻日益增大,受到越來越多人文社科學者的熱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社會背景、新技術、新思想而來的,以“緩慢漸進”說為代表的新工業革命史研究范式對之前的研究進行了系統的反思和批駁,并逐漸成為了一種主流觀點。本文擬對20世紀70年代后的工業革命史研究新范式進行考察,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一、新范式產生的條件
學術范式的轉移無疑是由復雜的多種因素合力推動的。從時代背景來說,20世紀70年代后,英國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經濟上將近20年的高歌猛進,由海灣戰爭等因素造成的滯漲(stagflation)現象長期存在,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百試百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飽受質疑。[2]民眾對經濟形勢信心不足,就連大部分學者也惴惴不安。
沃特·羅斯托(WaltRos-tow)就曾郁郁地感嘆“:在20世紀70年代,突然之間,社會上一切對于經濟增長的正當性以及信心都煙消云散了。”[3]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工業革命史家開始看衰工業革命,質疑當時經濟增長速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①盡管如此,社會背景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只能說是間接性的,畢竟不論史學理論怎樣進步,力求實踐中史學研究的客觀化是史家的基本操守之一。
依筆者之見,直接影響工業革命史研究范式轉換的原因有三條:首先,20世紀70年代之前大量新資料、新數據的發現及整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思想首先受到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Hill)以及E·P·湯普森(E.P.Thompson)等左派史家的重視。
經過他們的介紹和傳播,年鑒學派的影響漸漸地在英國史學界蔓延開來。受到年鑒學派影響的英國史家認為,以德國蘭克學派②為首的傳統史學過于將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檔案等材料,眼界狹窄,而當下的新史學應該建立在大量收集除官方外各種民間及非官方的社會、人口、經濟等數據的基礎上。[4]22簡言之,新史學需要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數據,從而發現并把握社會較長時段的發展規律。
受此影響,在1964年,一批人口統計學家和歷史學者建立了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研究小組(theCambridgeGroupfortheHistoryofPopulationandSocialStructure),開始了一項長達40年的回溯性研究計劃,收集并整理不列顛400年的家族史。其中,整理出的16-19世紀有關社會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材料數占了總材料數的2/3,這些成果最后都有利地推動了工業革命史的研究。[5]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也以堅韌的毅力開始整理自己所能涉及的材料。就工業革命史而言,范斯坦(Feinstein)收集了關于工業革命時期資本形成的資料,林德特(Lindert)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收集了關于社會與工作結構的資料,瑞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爾德(Schofield)收集了關于人口變化的資料,哈利(Harley)收集了關于社會生產率的資料,波拉德(Pollard)收集了關于煤炭行業收入的資料……這些資料的收集和整理都毫無疑問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材料,難怪有學者指出類似于克拉夫茨(Crafts)①這樣學者的研究都是把“前人已經找到的積木搭起來”[6]。
不難看出,新范式的轉變確實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材料、新數據的發現與整理之影響,更多的材料讓20世紀70年代后的學者有機會重新審視工業革命的歷史,得出一個不同的結論。其次是經濟學研究方法在工業革命史研究中的使用。新數據的不斷擴大讓史學家在一個時段內感到無所適從,畢竟傳統史學方法并沒有為他們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
為此,最擅長處理和分析數據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工業革命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一股風頭強勁的量化史學風潮。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的執牛耳者們大多都有經濟學研究背景,甚至簡·德·弗里斯(JanDeVries)等人根本就是經濟學家出身,跨界研究工業革命史。
他們十分善于把一系列歷史事件簡化為數據集合中的元素,之后再用理想型的數據模型將看似雜亂無章的元素進行排列組合,最終整合出歷史規律。[5]不僅如此,他們還通過設立研究機構努力將計量方法傳給下一代史學家。
20世紀60年代后期,密歇根大學、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相繼開設了暑期講習班講習量化史學方法,美國歷史學會也專門成立了“定量資料協會”(QuantitativeDataCommittee),成為支持量化史學發展的重要學術陣地。在這些協會和講習班中,作為經濟史研究的重頭戲,工業革命史研究被拿來作量化史學范例進行講解的時候不在少數。[5]
到了新世紀,J·D·克拉克(J.D.Clark),這位風頭不減當年的工業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帶著自己的觀點和量化方法來到北京大學開壇講學,成為了第一期北京大學量化歷史講習班的重要導師之一,開課的第一個主題就是量化工業革命。[7]可見,當下量化史學的發展和影響已經超出了西方學界,作為世界經濟史的最重要研究領域之一,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量化方法和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
第三,20世紀70年代后的工業革命史研究者普遍對之前在史學界起理論指導作用的輝格主義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不滿。輝格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是英國史學界20世紀70年代之前執牛耳超過一個多世紀的兩種學術思潮。
輝格史學是一種“通史概觀”,這種概觀以“當下為參照物研究過去”,并且認為所有的歷史事件“都顯示了數個時代以來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原則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是進步原則永遠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黨人則永遠對這一原則產生障礙”[8]10-11。
具體到工業革命史,輝格史學家認為工業革命是歷史線性進步的一個典型標志,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輝格黨人和新教徒送給世界的一份大禮。馬克思主義史學和輝格史學有所不同,它著重強調的是革命史觀,強調工業革命前后世界的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
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在福柯等后現代史家的影響下,當時的工業革命史學者竭力擺脫輝格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控制,力圖在眾多新數據的支持下找出工業革命前后的社會聯系以及解決社會進步的幅度等問題,以客觀的史學實例給予輝格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以重擊。[9]這樣,客觀上新數據、新材料的發現和整理,結合主觀上經濟學方法的使用和反馬克思主義史觀、輝格史觀的史學思想,直接推動了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革命史家對工業革命認識范式的轉變。
二、新范式的主要特點
自1884年阿諾德·湯因比(ArnoldToynbee)遺作《工業革命演講集》出版到20世紀70年代之前,學者對工業革命史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樂觀派和悲觀派兩個學派。[10]422悲觀派以湯因比、哈蒙德夫婦(Hammonds)和韋伯夫婦(Webbs)為首,他們的童年時代就生活在工業革命的大潮中,對當時人們的困苦生活感同身受,因此在學術上對工業革命帶來的所謂“進步性”持批評態度。
碧翠絲·韋伯(BeatriceWebb)認為,“工業革命時期給人以巨大的,殘酷的,倒退的體驗,人們為此而生活窘迫,流離失所,身心交瘁,幸福不在。工業革命……被證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11]343-344。韋伯夫人的看法可以說是準確地道出了第一代工業革命研究者的心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工業革命史學者則和他們的前輩看法大相徑庭。
他們對工業革命沒有直接的體驗,卻感受著戰后西方經濟的騰飛與福利,這一時期的學者把發現的新材料和他們的主觀感受結合在一起,得出了工業革命是現代經濟騰飛的起點這樣的樂觀結論。他們的代表人物是羅斯托(WaltRostow),他認為“工業革命是一場起飛(take-off),它直接關系到生產方式變化”。
起飛是穩定增長的障礙和阻力得以最終克服的時期,起飛促進了巨大的經濟進步,并開始對整個社會產生支配性的影響。[12]20世紀70年代后的工業革命史對上述兩種工業革命的主流看法都持批判態度。首先,他們不同于湯因比和韋伯夫婦的悲觀論,而是認為工業革命時期確實是一個經濟增長的時期。
這是新范式的第一個特點。新范式的主導人物克拉夫茨(Crafts)認為“,毋庸置疑……到1840年,英國的就業體制(employmentstructure)已經和幾十年前發生了變化,也有別于歐洲其他國家”,“(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工業中最高的生產率和高出口率,農業中最低的勞動力比例,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實際上,英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9]。
克拉夫茨從宏觀的角度看待工業革命的進步問題,而這一時期的其他學者也從各自的研究方向出發,來闡述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增長。瑞格利(Wrigley)認為,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制度,即使沒有完全取代舊的制度,也在“大規模生產,新產品開發,強化對生產和消費者的剝削方面引人注目”[2]。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認為:“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不斷提高的勞動投入質量和資本投入質量……是明顯的。”[2]蘭德斯(Landes)最強調的是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變化,他寫道:“技術變化極大地增加了出口和產品與服務的種類,單單這一變化就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13]
即使像簡·德·弗里斯(JanDeVries)這樣直接對工業革命概念提出質疑的學者,也認為他所關注的焦點是這一時段經濟增長背后的原因——生產力的革命性突破還是僅僅增加了勞動量——而不是增長本身。[14]由此可見,對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工業革命史家來說,經濟增長論得到了他們絕大多數的認同。
新范式的支持者們不同意悲觀派的論調,卻也沒有對樂觀派的論調加以認可。相反,他們認為工業革命時期的所謂經濟騰飛只是樂觀派的一廂情愿。雖然經濟增長是不容否定的,但更顯著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遲緩。
更確切地說,緩慢發展是新范式的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同樣是克拉夫茨,在肯定了經濟的增長后,用一系列復雜的數據模型導出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經濟發展緩慢的結論。舉例來說,他認為英國1780-1800年間經濟增長率只有0.35%,而在之后的20年也沒有超過1.61%,這是因為全部要素生產率(TEP)①增長緩慢的緣故。
1760-1800年間,TEP增長只有0.2%。而1860年左右才勉強達到1%。他的估計和樂觀派學者相比低了大約2/3左右。[15]由此,通過一系列數據分析,克拉夫茨堅定地站在了樂觀派的對立面,并且不無諷刺地寫道:“工業革命時期經濟的增長和‘起飛理論’比起來簡直緩慢了太多。”[9]除克拉夫茨外,其他新范式的代表人物也堅定地支持緩慢發展。埃里克·瓊斯(EricJones)和隆多·卡梅隆(RondoCameron)都認為緩慢工業化是常態,爆炸性增長僅僅是當時發展的一個例外。[9]
A·穆森(A.Musson)則強調,時至1851年,消費品工業仍然殘缺不全,而且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產生于小作坊里;就業模式仍然十分單一,傳統的手藝人、勞工、家庭傭人無處不在;工廠制度和蒸汽動力的擴展都十分緩慢。“1850年的英國和1750年比起來,進步實在不大。”[2]
簡·德·弗里斯為了闡述工業革命時期經濟緩慢增長的理論,把工業革命置于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歷史框架之中,指出傳統上認為開始于18世紀后半期的工業革命,實際上是1500-1800年經濟緩慢增長的一部分,和之前的時段一樣,這種緩慢增長主要來自勞動時間與勞動量的增加,和所謂“大工業時代”、技術創新、社會變革沒什么關系。[14]
正如大衛·康納丁(DavidCannadine)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70年代后,有限增長和緩慢增長成了這一時期工業革命史學者的共識。新范式的第三個特點是這一時期的工業革命史研究專家首次對“工業革命”這個定義進行了艱深的思索和探討。時至1967年,羅伯特·哈特韋爾(RobertHartwell)曾不無遺憾地說,在他之前的工業革命史研究者“對工業革命定義的思考之少讓人感到吃驚”[16]。
的確,許多學者使用這個概念僅僅是因為史學研究上的約定俗成。20世紀70年代之后,成熟的緩慢增長理論讓工業革命史的研究專家開始細細地審視像“‘工業革命’一詞用以描述當時的時代是否恰當”這樣的基礎問題,而大多數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比如埃里克·瓊斯(EricJones)認為“工業革命一詞是不恰當的……這個詞給予了英國特殊的地位,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很少打上英國的印記,斷裂性出乎意料的少,連續性(continuum)占據著時代主流”[9]。
J·D·克拉克認為所謂工業革命,根本就是中世紀土地貴族財富和權利的傳承與交接,所以1832年之前,根本沒有什么革命可言,更沒有工業引導的革命。所以工業革命是個根本就不該存在的偽概念。[9]
除以上兩人外,對工業革命概念反思最深、用力最勤的學者當屬簡·德·弗里斯。簡·德·弗里斯認為,漸進變革的工業革命時代依賴于之前時代的長期準備,而且之前時代的增長方式和所謂“工業革命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并無本質的不同,所以應該將1500-1800年作為一個長時段進行分析,這300年來一直緩慢漸進的經濟需要在一個統一的維度之下被理解。
為此,簡·德·弗里斯提出“勤勞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的概念,希望能在更過闊的歷史背景之下代替“工業革命”。他指出,1500-1800年間經濟的緩慢增長主要是因為以家庭(household)為單位的勞動量的增加,而不是任何生產力的“革命性突破”。家庭作為一個最為基礎的共同居住與再生產單位,在資源的重新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勤勞革命本質上是家庭成員之間就時間與其他資源進行分配的決策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成員工作強度大,休息時間被擠壓到所能承受范圍的底線,相互剝削現象嚴重,從而在300年的漫長時光中緩慢創造財富,刺激消費,增加市場上商品種類,最終致使家庭產生新欲望和新消費形式,為后世走出勤勞革命作好鋪墊。[14]
總的來說,20世紀70年代之后,正如哈特韋爾觀察到的,工業革命(theIndustrialRevolution)這三個單詞的每一個部分都受到嚴苛的挑戰:曾經,“the”代表工業革命在英國最典型,獨一無二(Britishuniqueness);“Industrial”代表工業革命變化的最顯著特點;“revo-lution”代表變化的速度和全面性(speedandcompre-hensiveness)。
現在,工業革命不能僅僅被限制在英國,也不能僅僅被限制在工業方面,發展速度更是稱不上革命。[9]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20世紀70年代后的工業革命史研究強調經濟發展的緩慢增長,強調在此基礎上對工業革命概念的全面分析①。這些研究中的一致性以及和之前兩大最主要研究流派(樂觀派,悲觀派)的明顯不同使得他們自成一個陣營,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對新范式的評價
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革命史研究新范式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維、新結論的出現讓學者們認清了在此之前工業革命史研究的缺點和不足,也為今后的繼續研究鋪平了道路。但筆者在此希望能多談談新范式的缺點和局限性,對這些缺點的認真反思將是使未來研究更加客觀的前提之一。
依筆者見,新范式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使用的檔案數據本身存在先天不足。歷史學家的學術生涯是和資料與檔案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搜集到的檔案數據有自身缺陷是每個歷史學家都會遇到的事情。但對于20世紀70年代后的工業革命史研究者來說,這個缺陷尤其致命,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完全依賴于數據的量化,數據的缺失或者不可靠會使他們不得不面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境地。根據林德特(Lindert)估算,對于大型工業、農業與商業團體來說,對生產率的計算誤差可能會高達60%;而研究工業革命時期鞋匠、木匠等的生產率、生產成本等問題,情況基本上就比瞎猜好一點點。[15]
無怪乎就連克拉夫茨這樣的新范式執牛耳者,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研究很多結論僅僅是“最靠譜的猜測”(bestguess),而非找到了確切的證據(definitiveevidence)。[6]其次,研究者本身的思維漏洞。資料缺乏與不準確固然是極大問題,新范式代表者們研究的思維漏洞也不容忽視。
比如,包括克拉夫茨、瑞格利、林德特、威廉姆森等人在內的學者在研究工業革命時期生產率增長、家庭生活水平、工廠制度內部結構等問題時,都僅僅考慮了當時成年男性的產出、工資分配和工齡等情況,卻對有關女工和童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置若罔聞,這部分材料確實很少也很難找到。畢竟,在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方面,工業革命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毫無疑問,對這部分人研究的缺失將造成重大的研究誤差。[15]
再如,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各地發展水平不一,而且許多地區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工業體系。拿約克郡(Yorkshire)來說,它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成衣行業的發展、組織方式的變革以及工業與商業的緊密聯系。[15]但新范式的代表人物們(克拉夫茨首當其沖)往往都在使用宏觀經濟學方法,只利用全國性的數據,在國家的框架下進行研究。
這種研究方法根本無法把握國家內地區發展的活力和獨特性,使得他們不能完全洞悉工業革命的地區性特點,進而忽略一些地區的飛速發展,使自己的研究立論大打折扣。由上可知,新范式的缺陷和它代表人物的思維漏洞有著密切的關系。
再次,新范式的研究方法單一,研究內容只限于經濟問題。歷史學研究當然需要借鑒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但絕不能被這些方法主導。克拉夫斯、林德特、埃里克·瓊斯等人都認為研究工業革命和研究經濟是否增長、增長幅度如何是一回事,所以對他們來說,工業革命研究基本等同于量化經濟增長問題。[6]
但歷史學畢竟有其獨特之處,她關注的是經濟運行結構的變化,關注的是這些變化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互動,關注的是過去的社會,關注的是冷冰冰的數據背后推動社會發展或后退的原因。工業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就如庫茲涅茨(SimonKuznets)所言:“這一時期①文化環境(culturalmilieu)的變化……可能比儲蓄與資本的積累更加漫長也更加痛苦……更能代表這個時代。”[6]所以使用單一的經濟方法進行單一的經濟增長研究注定只是管中窺豹,不能對工業革命進行全面的理解。最后,客觀的史學研究不能和先行的意識形態問題糾纏在一起。
部分新范式的代表人物是帶著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和輝格史學的“怒氣”來研究工業革命史的。比如J·D·克拉克,當他還是個研究生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史學和輝格史學充斥著英國史研究的各個角落。千篇一律的研究方式使得年輕且才華橫溢的克拉克對這兩種當時起支配地位的史學研究方法十分不滿。
當他終于在學界聲名鵲起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和輝格史學所最為重視的兩次革命——英國光榮革命和工業革命就成了他畢生攻擊的目標。他甚至把工業革命說成是假革命(spuriousrevolution),應該從歷史中無情的抹去。[9]這種被憤怒、被意識形態問題沖昏頭腦的事情是歷史學研究的大忌,也是不管哪個史學學派、哪種史學研究思潮都應該竭力避免的。正視自身存在的缺點和局限性,20世紀70年代后工業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才能擁有堅實的基礎,不至淪為空洞無物的清談。
參考文獻:
[1]KUHNT.TheStructureoftheScientificRevolution[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
[2]CANADIANED.ThePresentandthePastintheEnglishIndus-trialRevolution[J].PastandPresent,1991,(103):131-172.
[3]ROSTOWW.GettingfromHeretoThere[M].NewYork:Mc-Graw-Hill,1978.[4]BLOCHM.TheHistorians'Craft,translatedbyP.Putnam[M].Manchester:ManchesterPress,2011.
[5]ANDERSONM.QuantitativeHistory[M]//WilliamOuthwaite,StephenTurner.TheSageHandbookofSocialScienceMethod-ology.London:SagePublicationLtd,2007.
[6]HOPPITJ.CountingtheIndustrialRevolution[J].TheEconomicHistoryReview,1990,(43):173-193.
工業革命論文投稿期刊:《工業技術創新》是工業和信息化部主管、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主辦的國家級科技學術類期刊。本刊主要面向工業技術創新領域的有關工業主管部門、工業企業、科研創新的學術交流平臺、技術創新成果的宣傳轉化園地和戰略政策研究的理論探討陣地。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