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急管理機構的變遷與發展
時間:2020年12月31日 分類:科學技術論文 次數:
一個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的演變與該國的國情以及安全環境(占主導地位的威脅類型)有密切的關系,美國國土面積與我國相當,科技、經濟實力強大,同樣處于公共安全與自然災害形勢復雜的背景下。 經過長期災害應對實踐的積累,美國在應急管理的很多方面都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我國在公共安全和自然災害應對方面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亟須建立并發展綜合高效的應急管理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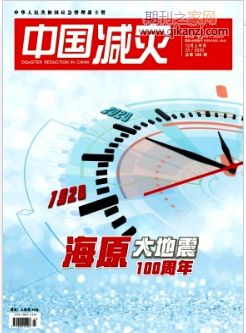
從2007年,我國應急管理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出臺至今,我國的應急管理經歷了多次突發事件的考驗。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部的成立拉開了“多災種、大應急”管理體系頂層設計的序幕。 但如何在整合機構組織的基礎上,切實推進應急管理業務融合,在整個社會層面,實現綜合高效應對各類突發事件,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到目前為止,國內已經有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美國的應急管理體系進行了歷史沿革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但對于大量的基層應急管理從業者和民眾而言,美國的應急管理機構的變遷與發展仍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為此本文在綜合國內諸多學者對美國的應急管理工作研究的基礎上,從科普的角度再次梳理美國的應急管理體系的演變歷程,以期為更多的應急管理從業者及社會公眾提供有價值的信息,為全社會減災文化和減災能力的提升盡微薄之力。
基本概念
應急管理是對資源和責任的組織和管理,針對突發事件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備災、響應及早期恢復階段(聯合國減災署,2009)。 根據王宏偉(2007)的研究,美國應急管理主要處理危及公眾健康、生命、財產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概念中同時包含“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危險要素管理”(Hazard Management)及“災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三個方面的含義。 風險管理側重減少危險發生的概率,危險要素管理側重限制危險發生的條件,災害管理側重減輕危險造成的影響與后果。 以地震為例,進行地震分區并給出相應的抗震設防標準屬于風險管理,對地震危險區的建構筑采取抗震措施屬于危險要素管理,設立地震避難場所、制定地震應急預案屬于災害管理。
這三方面的含義與美國應急管理范式(1978)中的減緩(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響應(Response)、恢復(Recovery)四個階段相吻合,體現了“預防為主”“防救結合”的原則,其中將風險消弭于無形之際的減緩是四個階段的核心。 這種范式在2011年擴展為預防(Prevent)、保護(Protect)、減緩(Mitigate)、響應(Response)、恢復(Recover)5個領域的制度性框架和跨部門行動預案。
應急管理體系是指與應急管理有關的事物及其文化意識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整體,具體體現在對上述四個階段所涉及的資源、責任等進行管理時形成的一系列組織機構和法律法規體系。 現代意義的應急管理并不涉及軍事沖突與戰爭,但美國的應急管理可以說是脫胎于民防制度。 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的民防體制為非戰時應急管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持續保持著割舍不斷的聯系。
組織機構演變歷程
依據應急管理與民防機構的分合和兩次重大變革(1979年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和2011年國土安全部的組建),美國政府的應急管理組織機構演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基本成型期(20世紀30—50年代)
20世紀初期,美國聯邦政府并沒有一個負責應急管理的機構,地方政府對應急救援負主要責任。 1905年,國會授權美國紅十字會參與負責協調災害救助行動,代表聯邦政府履行有限的救災職能。 這種模式意味著美國州和聯邦政府的災難救助基本上是一種道義行為,并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1933年,為應對經濟危機并救助自然災害受災民眾,美國成立了“國家應急管理委員會”(National Emergency Council),這是聯邦政府首個以系統化的方式處理災害事件的機構,也是一次系統化處理災害事件的嘗試(閃淳昌,2010)。
同期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兼顧減災,美國成立了“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以減輕洪災影響并發展水電,還出臺了《洪水控制法》,授權美國陸軍工程師部隊(US Army Engineering Corps)興建、修復防洪工程。 災害管理相關的機構還有“重建融資公司”和“公共道路局”(Bureau of Public Road)被授權負責發放賑災貸款以修復被災害毀壞的設施,包括公路和橋梁等。
1939年,經濟復蘇后,“國家應急管理委員會”更名為“應急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與新成立的“民防辦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聯合辦公,1945年被解散。
1947年,聯邦政府出臺《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奠定了美國國家安全體制的法律基礎。 根據該法,政府建立“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進行國防動員。
1949年,“民防辦公室”被“聯邦民防局”(Federal Civil Defense Administration)取代,“應急管理辦公室”作為民防局的一部分被重新組建。
根據《1950年民防法》(The Civil Defense Act of 1950)和《1950年災害救助法》》(The Disaster Relief Act of 1950),1951年,“聯邦民防局”成為聯邦政府的獨立機構,并進一步承擔了“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的職責。 同期成立的還有“國防動員辦公室”(Office of Defense Mobilization)。 這個機構的職責主要是戰爭時期負責關鍵物資的生產和儲備以及民眾的快速動員,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負責“應急準備”。
1958年,美國政府把“聯邦民防局”和“國防動員辦公室”這兩個相關機構進行合并,組建為“民防與國防動員辦公室”(Office of Civil and Defense Mobilization)。 至此,美國安全應急管理體制中的組織機構基本形成(汪波,2013)。
(二)分治混亂期(20世紀60—70年代末)
20世紀60年代,美國自然災害頻發。 1960年蒙大拿州發生7.3級地震; 同年,颶風“唐娜”襲擊了佛羅里達西海岸; 1961年颶風“卡拉”橫掃得克薩斯州。 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白宮內設立了“應急規劃辦公室”[1968年改稱“應急準備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將民防和自然災害分開,專門處理日益增加的自然災害風險,但民防仍然在應急管理中占主要地位。 直到70年代初,美蘇關系出現緩和后形勢才有所轉變。
1962年,風暴“圣灰節”(Ash Wednesday)席卷美國東海岸620英里的沿海地帶,導致的經濟損失高達3億美元; 1964年,阿拉斯加發生里氏9.2級地震,并在太平洋沿岸引起海嘯,造成123人死亡; 1965年和1969年,颶風“貝齊”(Betsey)和颶風“卡米爾”(Camille)造成墨西哥灣數百名美國公民喪生及巨大的經濟損失。 聯邦政府仍然是通過臨時立法向災區提供災害援助。 1971年圣費爾南多6.5級地震造成64人死亡,千余人受傷,城市生命線系統大量破壞,經濟損失高達10億美元。
1972年聯邦政府成立“防務民事準備局”(Defense Civil Preparedness Agency)取代了“民防與國防動員辦公室”。 各州及地區獲得的撥款一半用于民防,另一半用于應急。 民防工作人員被要求協助各州及地方政府制訂應對自然災害及核打擊的計劃。
1974年,美國中西部爆發的龍卷風使數百人斃命。 1977年,田納西河流域遭受巨大洪災,發生多起崩壩事件。 1979年,賓夕法尼亞州三里島發生核電站事故。 而同期美國的應急管理職能被嚴重分散(表1),有100多個聯邦機構不同程度地參與各類災害和事故的應對與處置。 機構職能分散、政出多門、“勢力范圍”之爭頻繁出現,管理中的混亂延伸到州和地方政府一級,嚴重影響到應急管理的效率。
(三)整合發展期(20世紀70年代末—21世紀初)
1977年,全美州長聯合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指出:美國缺少全國統一的綜合性應急政策。 次年,該聯合會發表了《1978年應急準備計劃:最終報告》,建議聯邦、州及地方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以推行“綜合性應急管理”; 創建一個聯邦應急機構,其職能包括減緩、準備、響應與恢復; 在各州建立相應的機構。
1978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將3號重組計劃(3 CFR 1978,5U.S. Code 903)轉交美國國會。 該計劃明確提出將減災、備災與應急行動歸并為一個聯邦緊急管理機構,設立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主管由總統直接任命。
1979年FEMA正式成立,合并了國家消防管理局、聯邦保險局、聯邦廣播系統、防務民事準備局、聯邦災害援助局、聯邦準備局等部門。 并承擔了許多新的應急準備與減緩職能,如監督地震風險減除計劃,協調維護大壩安全,協助社區制訂嚴重氣象災害的準備計劃,協調自然與核災害預警系統,協調旨在減輕恐怖襲擊后果的準備與規劃等。 FEMA的首任主管約翰·馬西提出“一體化的應急管理體系”(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EMS)的概念設想,強調將自然風險準備與民防融合起來,使指揮、控制與預警功能適用于各種突發事件,包括應對核打擊。
王宏偉(2007)、閃淳昌(2010)認為FEMA的成立體現了美國應急管理的一種全新理念,即“綜合性應急管理”(全災種與全過程管理),標志著美國應急管理真正走上了綜合型應急管理的軌道。
但機構組建容易、與之相關的各種紛繁復雜的項目、計劃、政策以及人員運行模式和組織文化整合則是一項規模巨大的工程,需要領導者卓越的領導能力和統攬全局的宏觀視野。 同時,在整合相關部門和相關法規時,FEMA還受到國會23個委員會以及小組委員會的監督和限制。
FEMA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組織性立法來支持其運作,許多部門各自為政,對災害應對不能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同時1982年起美蘇關系再度緊張,二、三任主管任職期間,FEMA仍延續了國家安全優先模式。 盡管在減災方面表現平庸,1988年通過的《斯塔福德減災和緊急援助法》(T.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and Emergency AssistanceAct)仍賦予了FEMA更多的權限和專項財政預算支持。
該法不僅明確界定了聯邦政府在救災和減災工作中救助的內容、對象、范圍和條件等,而且對FEMA的工作做出了更為明確細致的界定,將綜合應急管理體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為該機構持續深化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發展。
但在1989年9月颶風“雨果”、10月洛馬·普雷塔7.1級大地震兩次災害應對中,FEMA的遲緩響應、對有些小災害甚至不予響應的狀態使其受到公共輿論的嚴厲批評與譴責。 在核威脅逐漸淡去、災害應對能力遭受嚴重質疑的背景下,FEMA的改革壓力空前巨大。
1993年,美國公共管理國家研究院和美國總審計署針對FEMA發布三份報告,對FEMA是否應當被解散; 軍隊在災害中應該發揮什么作用; FEMA與抵御核打擊的民防在災害中應該發揮什么作用; 聯邦應急管理職能如何才能得到改進; 如何建立與州及地方應急管理機構之間的關系、改進與白宮及國會的關系等涉及改革的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
同年,一位具有豐富應急管理經驗的主管(James Lee Witt)掌管FEMA大權。 他將FEMA重新定位成一個高效和快速反應的部門,針對損失與需求估價不充分、溝通不暢、法律授權不清晰、州及地方的應急反應者缺乏訓練等問題,實施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機構內部,打破機構之間各自為政的局面,對機構進行內部重組; 組織所有工作人員進行相關的安全應急業務訓練。 在災害服務領域大膽地采用新技術,建立安全應急管理的信息網絡,突出強調應急管理的風險減緩的作用; 在外部,特別重視廣泛合作,加強了與各州及地方應急管理機構的聯系,對任何災害都提供快速、有效的回應,建立了與國會、媒體、志愿者組織、私人部門的新型合作關系。 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聯邦應急管理局起死回生。
1993年美國中西部遭受大洪水,九個州成為重災區,并宣布進入重大災害狀態。 FEMA成功通過自愿購買和搬遷項目,使民眾搬離洪水受災區,為應急管理的重點從災后恢復轉變為災前減損提供了契機。 1994年,在應對加利福尼亞州的“北嶺地震”中,充分發揮了信息快速全網傳遞的新技術,實現災情信息共享,減輕了地震災害的影響。 此后FEMA主管升任內閣成員,州和地區急管理機構的領導人也進入各州和地方政府內閣,確認應急管理部門在政府體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
1997年,FEMA發起了一項名為《沖擊性項目》國家倡議,推動一種新的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法,該項目致力于提高社區抗災能力,旨在將應急管理和減災措施融入美國每個社區。 這種將社區作為減災基本單元的思想對后續美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至2000年,美國的駐外機構和海外軍事設施屢遭恐怖襲擊。 國內,1993年,紐約世貿中心就發生過第一次爆炸。 1995年,俄克拉何馬市中心的聯邦機構大樓發生炸彈爆炸事件,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派出包含665名救援人員的11支城市搜索與救援任務組開展援救和恢復工作。 由于對恐怖主義到底是災害、犯罪還是戰爭存在爭議,反恐準備的牽頭部門遲遲不能落實。 州政府希望FEMA牽頭,但FEMA因處理諸如化學、生物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具體問題所需的資源和技術超出了當時應急管理的范圍而猶豫不決。
1996年出臺的《南恩—盧格法》(Nunn-Luger)要求FEMA、司法部、健康與人員服務部、國防部、國民警衛隊等機構共同承擔反恐職責。 1998年國防部和司法部共同成立了“國內準備辦公室”。 2000年,布什當選為總統,成立了“國家準備辦公室”,與“國內準備辦公室”共同工作。 制訂了各自的反恐計劃,而反恐事件的領導機構,包括火災、警察、應急管理或應急醫療服務等并未明確。
2001年1月,《國內反恐行動計劃》將反恐職能細分為危機管理和后果管理,前者以司法部為首負責識別針對美國及其民眾的恐怖主義風險源,突出執法作用; 后者以FEMA為主負責對災害中遭受損失的美國公民提供救援及恢復援助,突出應急管理職能。
(四)重組提升期(21世紀初至今)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震驚了整個美國,也徹底打破了美國的傳統安全觀,美國應急管理體制迎來重大變革。 2001年,美國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 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簽署《國土安全法》,正式啟動了美國50年來最大規模的政府改組計劃。 2003年1月,國土安全部正式成立,整合了來自財政部、國防部、司法部、交通部、能源部等8個聯邦部門的22個機構的職責,擁有近18萬名編制人員,成為美國的第17個部。
重組后國土安全部雖然在備災目標、應急響應計劃、規范技術系統方面發布了一系列文件,但以反恐為核心確定備災目標和任務職責,某種程度上違背了整合反恐與救災的初衷。 以政府部門為主體提供公共安全產品,背離了應急管理全社會參與的原則。 FEMA的長處沒能得到發揮,預算被縮減,人員和資源也被轉移到其他反恐項目中。
2005年8月,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難——卡特里娜颶風登陸,幾乎摧毀了整個海灣地區,颶風最終造成1000多人喪生,經濟損失達250億美元。 這場災難是對國土安全體制下美國應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檢驗,引發應急管理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2006年,美國政府發布了關于“卡特里娜”颶風的調查報告《聯邦政府對卡特里娜颶風的響應:經驗與教訓》,在此基礎上,總統簽署《后“卡特里娜”應急管理改革法》(The Post-Katrina Emergency Management Reform Act of 2006),這次改革矯正了“重反恐,輕減災”的偏差,在聯邦法律上重新確定了“聯邦應急管理局”的地位。 緊急狀態下,FEMA可以提升為內閣及部門,主管直接對總統負責。
每年為FEMA提供80.2億美元預算,要求其承擔起美國安全應急體制改革的兩項基本目標(建立一種充滿活力的全新的安全應急理念和一個綜合性的全國安全應急機制),在全美設立10個區域運行中心,負責與州以及地方安全應急機構聯系,共同制訂救援計劃,協同地方組織實施救助,負責評估災害損失等工作。 這樣的美國應急管理機構組織一直沿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美國政府總結自身應急管理工作和日本政府地震應對中存在的問題,以加強準備工作為導向,推進核心能力建設為內容,對應急管理的理念和戰略安排進行了重構,是在既有組織機構的基礎上對應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大提升。 這次重構的重點有三方面(游志斌,2015):
1.正式確立了“全社會參與”(Whole of Community)理念。 明確界定了全社會參與的概念和具體的參與主體,全社會參與是指一種包括居民、應急管理實際工作者、組織和社區領導者,以及政府官員能夠共同理解和評估各自社區的需求,并決定用最好的方法來組織和保護他們財產、能力和興趣的方式。 全社會參與的主體既包括個體和家庭,也包括以信仰為基礎的社區組織; 非營利組織; 學校和研究機構; 媒體; 還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部落政府、領地等在內的政府,并將其落實在具體的應急管理政策中。
2.正式明確了把“國家準備”(National Preparedness)作為基本戰略和具體目標。 把全國應急準備工作納入到整個國家的安全戰略中,并制定了具體的準備目標,使得應急管理成為鞏固美國國家總體安全的一項基本戰略。
3.重新構建了規范性、指導性和支撐性的文件體系。 對已有的應急管理的重要文件進行了重新審定或更新,使應急管理的工作文件體系更加清晰、翔實,更符合加強全國應急準備和提升核心能力的需要。 包括《全國準備目標》(National Preparedness Goal,NPG)、《全國準備系統》(National Preparedness System,NPS)兩份核心文件,明確界定了新的核心能力,以及建立能力的方法和途徑。
同時每年發布《全國準備報告》(NPR)對年度準備情況和核心能力進行審查評估; 將原先國家總體預案性質的(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響應框架,分解充實為覆蓋預防(Prevent)、保護(Protect)、減除(Mitigate)、響應(Response)、恢復(Recover)領域的五個政策框架和五個跨部門行動預案; 完善了一批技術支撐和指南文件,如指導如何制作應急預案的《綜合準備指南101(2.0版本)》; 指導如何開展風險分析與評估的《綜合準備指南201》; 指導如何開展信息傳遞和資源整合的《綜合準備指南502》等文件。
災害處理論文投稿刊物:中國減災是減災工作刊物。旨在宣傳黨和國家減災工作方針,指導全國減災工作,進行減災學術研究,提供國內外減災信息,普及減災知識,提高全民減災意識,宣傳我國減災工作成績,進行國際交流。
結語和討論
從1933年,聯邦政府首個以系統化的方式處理災害事件的機構成立至今,經過了將近90年的發展歷程,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符合美國國情的應急管理體系。 本文僅從管理機構的演變發展角度進行了科普式梳理,這種演變和國情、災情是緊密結合的,涉及減災理念的演變,最后對應急管理最近的核心理念和支持性文件做了簡單的介紹。 管理機構的變遷只是美國應急管理體系演變的一個方面,緊密相關的還有法律法規以及預案及其技術支持系統的演變,法律法規是機構得以成立和有效運轉的基礎保障,相應的操作層面的技術與文件支持是應急管理在實踐層面順利推進的保障,這些是密不可分的。
我國在如何構建符合國情、災情的綜合性應急管理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 我國“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方針與美國是一致的。 2016年以來,黨中央提出了三個工作轉變方向——“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并發表一系列重要的講話,對于政府的執行力,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的是加強體系和能力建設、增強責任意識。 以這些指導思想為基礎,如何利用我國的制度優勢,進一步明確應急管理的理念、目標、戰略規劃,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促進組織機構的有效運行,在實踐層面出臺更具靈活性、實用性、操作性的支持文件仍需要專家學者特別是相關從業者持續不斷的努力。
作者:謝天琳 任志林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