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境背景下辜鴻銘的三重文化使命
時間:2017年12月01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辜鴻銘是一個"內中外洋"的文化混血兒。 在文化危機深重的社會環境下,他采用西方話語承擔起作為一個文人的責任與使命。縱觀其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動,他始終在這樣的一條文化道路上進行抗辯:追尋個體身份認同,重塑民族文化自信,探索人類文明走向。 盡管他將建立社會文化秩序的期望一廂情愿地寄托到儒家道德文明之上帶有烏托邦色彩,但置于整體歷史語境下可以從他獨特的話語形式中看到其思想的超越性。
關鍵詞:辜鴻銘,文化使命,西方話語,現代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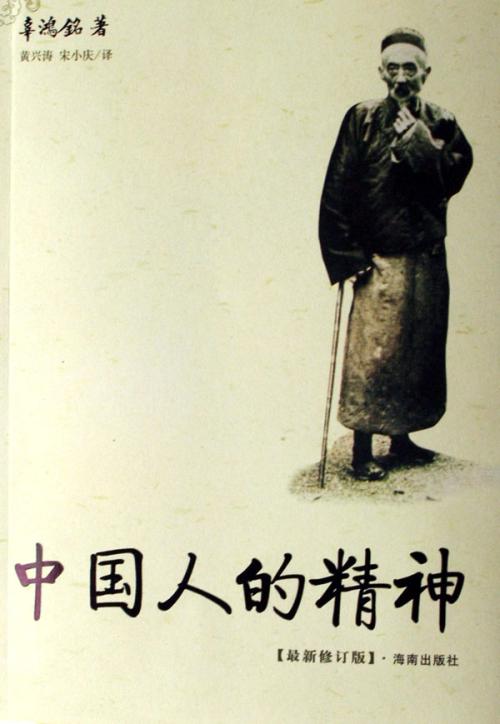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在歐洲文化風暴的侵襲之下,中國傳統文化體系遭受到巨大的打擊。同時,政治上的節節失利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近代知識分子在探尋民族自新之路的同時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將目光紛紛投向西方社會,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文化危機。西方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較量造成了近代中國復雜的社會文化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各種社會思潮此起彼伏,各種聲音充斥著當時的中國社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辜鴻銘以一個文人的高度自覺和責任感,承擔起歷史所賦予的文化使命,嘗試從文化層面重建已經失序的社會范式。
一、辜鴻銘的三重文化使命
辜鴻銘生于南洋,學于歐洲,入張之洞幕,任教于北大,與托爾斯泰、泰戈爾、毛姆、芥川龍之介等西方名流保持交往,是清末民初兼通中西文化的中國第一人。比起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他一生的文化事業更值得世人稱道。辜氏終其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不僅用英文進行,還積極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他將中國經典文本翻譯到西方,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進而尊重中國文化,又將西方現代性觀念引入中國傳統文化血液之中,從"他者"的文化角度打開對"自我"認知的新視野。然而辜鴻銘卻面臨著這樣三方面的文化危機:之于他個體而言的身份認同危機;之于民族而言的民族文化危機;之于人類而言的人類文明危機。因此,從主觀意圖來說,他一生的文化活動無疑圍繞著這樣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對個體文化身份的追索是辜鴻銘之于其個體的文化使命。華僑世家的淵源、混血的身份、以及早年留學歐洲的經歷使辜鴻銘不可避免的遭遇身份認同危機。然而回國之后他亦被同胞視為"非我族類"。辜鴻銘第一次拜見張之洞時,就被劈頭質問"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并讓他"趕緊脫掉西裝,留辮子、學官話、做個像樣的中國人"[1]32。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辜鴻銘始終被看作是文化的"局外人",正如艾愷所說,辜鴻銘"既非西方亦非東方的","乃一沒有安全感的'外人'"[1]357。
因此,他要不斷地證明自己是一個地道的、真正的中國人。進入到文化實踐上,他一方面蓄辮易服,深入研究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甚至有些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其予以偏袒,正是希望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極端肯定來獲得自我認同;另一方面,通過中西文明比較,對西方現代文明進行激烈地批評與譴責來加強這種認同感。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我們不能在孤立狀態下炮制文化認同",任何層面上的認同(個人的、部族的、種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與'其他'---與其他的人、部族、種族或文明---的關系中來界定"[2]。
清末民初,時代激蕩以及西方學者對中國人、中國文化的諸多偏見和輕視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形成文化自卑心理,一時間"西學東漸"蔚然成風。在這股熱潮中辜鴻銘猶如一個時代的逆子,極力贊揚中國傳統文明及道德價值,向西方弘揚中國文化,批判西方現代文明。為拯救民族文化危機,他做了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大力闡釋儒家道德文明價值。他認為儒學中存在像宗教那樣能給眾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東西,雖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而孔子的君子之道"是一種精純有序的、比哲學家和倫理家的道德法更為深刻、更為高級的法則"[3]260。
其次向西方譯介儒家經典,經黃興濤先生考證,辜鴻銘向西方完整譯介的儒家經典有《論語》《中庸》《大學》。并在儒經西譯中表達了這樣的愿望,即"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但愿在耐心讀過我們這本譯書后,能引起對中國人現有成見的反思,不僅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于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際交往的態度"[3]37。再次,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他認為歐洲近代文明是比物質文明還要次一等的機械文明,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建筑在金錢之上,"歐洲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后義"[3]357等。
盡管辜鴻銘的思想不乏偏頗之處,但這一系列文化活動在當時"充滿了弱小民族反抗文化歧視的民族正氣"[1]60-61,糾正了長期以來外國傳教士及漢學家對中國人、中國文明的誤解,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對傳統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從文化層面對民族所承擔的責任和使命。
辜鴻銘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要挽救的并非中國,而是整個道德文明"[4]。按照歷史學家湯因比對人類社會的分期,彼時的西方正處在"現代"向"后現代"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入發展,使歐洲社會的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工業文明的弊端不斷暴露,社會倫理道德體系崩潰。一戰的爆發更促使西方陷入深重的文化和信仰危機。整個歐洲彌漫著悲觀的情緒以及對現代文明的憂慮與反思。
面對日益嚴重的價值失落,當西方學者將目光轉向東方尋求治療之道時,辜鴻銘已經嘗試從東方傳統文化中尋找可能。他表示研究中國文明"將有助于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困難,從而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3]228。對于人類文明的走向,辜鴻銘作出了這樣的預測,他深信東西方的差別定會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這個時刻即將來臨,這是所有有教養人們的義務。而他的奮斗目標正是促使"東西方文化的長出結合在一起,從而消除東西畛域"[3]403。
由此可見辜鴻銘的文化觀充滿了對人類整體文明的關懷。在近代中西文化沖突的社會環境下,當中國學者還囿于"中西取舍"問題時,辜鴻銘在文化發展觀上超越這一思路[5]。值得注意的是辜鴻銘多番比較東西文明的優劣并不是為了一較高低,而是為了在這種對照中尋找各自文明的弊病,從而構建一種普世的道德文明,挽救東西方現代文明危機,這是他對整體人類文化命運所承擔的文化使命。
二、文化使命的話語表達
辜鴻銘的成長和教育經歷主要來自西方。十三歲時辜鴻銘就被英國人布朗夫婦帶往英國留學,在西方呆了十一年,并游學于歐洲多國。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辜鴻銘已經形成了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因此,在個人表達上他顯示出這樣的鮮明特色:以"他者"的目光來觀照"自我",即采取西方的話語形式來認識并闡釋中國傳統文化,從這種話語形式的差異中尋找不同文明的弊病與可能的出路,從而更好地承擔起文化使命。
辜鴻銘一生主要以英文,其主要思想活動和文化訴求也主要來自于這些英文作品,如《尊王篇》《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國人民的精神》《吶喊》《中國學》以及一些講演集和論集等,而當前國內出版的多為中譯版。因而這里出現了幾次奇妙地語言折射現象。首先是以英文譯述中國傳統文化。這是第一次語言折射,如他在翻譯《論語》時所說的,他是以英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翻譯的,為了盡可能地消除由語言文化帶來的陌生和古怪,他盡量都去掉那些中國專有名稱。其次,中國人在接受辜鴻銘的這些思想時,無論是在翻譯或閱讀中,又按照東方的話語形式接受這些英文表達,這是第二次語言折射。最終的結果是,呈現在外國人面前的是較為純正的東方思想文化,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則是帶有現代性的西方話語。
根據黃興濤從"理性"的角度對現代性的把握,他認為"現代思維理性"或者叫"思想現代性"包括現代思維方式和現代基本概念兩個方面的內容[6]128。辜鴻銘在表達文化使命中就體現了這種思想現代性。辜鴻銘的文章中出現了很多現代基本概念,這些概念大多重視嚴密的定義,而排斥"妙不可言"之類帶有玄妙意味的表達,并且凝聚了現代性的核心價值。例如,在辜鴻銘看來典型的中國人是溫良或文雅(gentle)的,并明確地指出這種溫 良 文 雅" 乃 是 同 情 (sympathy) 與 智 能(intelligence)這兩樣東西相結合的產物"[3]237;"君子之道"是人的名分意識和榮譽感;"恬靜如沐天恩的神圣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等。由此可見,辜鴻銘每拋出一個概念時都會給出準確的定義,在其劃定的界限進行詳闡,而不是圍繞概念進行一些外圍的非確定的表達。像"溫文爾雅""赤子之心""道"等表達則往往給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另外像"理性""社會秩序""權利""無政府主義""群氓崇拜"等具有現代性核心價值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更是俯拾即是。
辜鴻銘的思想現代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的現代思維方式上。從小接受的西式教育已經將西方現代思維中的思辨性和批判意識滲透到辜氏的血液之中。以《中國人的精神》為例,辜鴻銘就巧妙地運用了歸納與演繹的思維方法,他通過中國人實際生活中語言、記憶力、講禮貌、不精確等方面的例子得出一個假設: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由于這種生活形成了淳樸的個性,進而發現中國文明中調和人的心靈與理智之間關系的機制---儒教,再深入闡釋其如何承擔宗教的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的闡釋再回到中國人的精神本質上是一種心靈狀態。在辜鴻銘那里每一個結論的得出都經過了嚴密的論證,每一步的論證前后都環環相扣,一步步演進,而不是思維的任意彌漫。這種嚴密的邏輯思維方式本身就排除了感性的隨意性,而具有理性色彩,因此思辨性和批判意識更強。
從具體的研究手法上看,辜鴻銘采用的不是考據訓詁,或尋章摘句,而是宏觀性的比較研究,將對象放置在與他者的對照中觀照。他將中國的儒學與西方的基督教比較,將中西義利觀進行比較,將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將東西方人的人生態度進行比較,將東西方的個人生活、教育、社會、政治、文明等方方面面進行比較。這種互為參照下所獲得的認知往往更加全面、清晰、客觀。例如辜鴻銘在闡釋中國人深沉、博大、淳樸、靈敏的性格和文明特征時,是通過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比較來闡釋的,在這種比較中不僅能清晰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還能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人的文明特性。
三、歷史語境下的重估
從話語形式的角度對辜鴻銘的文化使命進行解讀,可以發現,雖然辜鴻銘一些具體的文化觀和思想主張帶有烏托邦色彩,但將其置入到人類整體的歷史語境下進行重估,從他獨特的話語表達形式中,我們卻能發現辜鴻銘個人思想的超越性。從辜鴻銘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動來看,他把人生中三個層次的文化使命都寄托在儒家傳統道德價值上:從儒家文化中獲得身份認同,以弘儒來反抗來自西方的文化蔑視,在儒文化中尋找拯救現代文明痼疾的良方,探尋人類文化未來命運與走向。從當時中國社會的文化現狀來看,傳統文明的危機不僅來自西方文化的沖擊,更重要的是傳統文明本身的一些弊病。對此,辜鴻銘不加選擇地偏袒認同,這與當時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的社會主流思想顯然是不相適宜的。
因此,他的個人訴求在當時是很難獲得周圍人認同的。另外,為了反擊西方對中國人的偏見與誤解,辜鴻銘常常采用極端的方式詭辯,這種口舌之辨并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西方對中國文明的態度。最后他在人類文明出路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走進了一個誤區,狹隘地理解文明的內涵:拋開物質文明,過分鼓吹精神文明和道德價值。辜氏深受英國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強調情感、精神以及心靈,單純期盼從道德層面以精神力來重整東西方社會秩序,這種想法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從主觀上來說,辜鴻銘和當時所有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一樣都承擔起了時代所賦予的文化使命,但他因為思想中的種種不合時宜也受到來自各方的撻責與嘲弄。
辜鴻銘因"保王尊孔宣儒"的文化立場一直深受詬病,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保守主義的文化思想中沒有可取之處。筆者以為,從他的話語形式中可以發現他思想中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而這正與他的文化使命相一致。在現代話語之下,辜鴻銘在這些層面的表現出超越性:世界視野、主體意識、現代批判精神。辜鴻銘對中西文化的研究與闡釋并不是將其作為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放在人類整體文明中去觀照。這種世界視野在當時來說是少見的,而對當下我們在中西文化關系認識方面仍具有啟發性。哈貝馬斯認為主體性是現代的原則,而主體性則表現為個體主義和批判的權利[7]。
無論是他對個人文化身份的追求還是強烈地維護民族尊嚴的意識都是個體主義的體現。另外這里批判不是批評指責,而是批判地辯證地去認知世界。在總體文化觀上,辜鴻銘呈現出"撻西揚中"的態度,但他否定的只是荒廢了古希臘文化修養的現代歐洲近代文明,辯證地看待歐洲文明中的不同層面,"我所說的歐洲文明不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歐洲文明,不是這種不健康的文明,而是真正的歐羅巴文明"[3]397。對他所推崇的儒家文明,也沒有全盤肯定,盲目崇拜,他直指重知不重心的"亂道之儒"對中國文明的毀滅。因此,他思想中的超越性使他與當時的封建頑固派、國粹派、東方文化派、新儒學是不同的。
從社會轉型的層面來說,辜鴻銘的文化訴求和話語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在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思想現代性'的引入往往成為其社會逐漸走向現代化道路的推動機"[6]129。辜鴻銘的文化理想從本質上來說是要解決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化轉型中的混亂無序狀態,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不過是他選擇的一條道路,最終目的還是實現現代化。
在風詭云譎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辜鴻銘像一個文化的"混血兒"游刃于東西方文化之間,扮演著東西文化電鍍匠的角色,無愧于他作為一名有知文人應擔負的時代使命。他在文化領域的探索給我們展現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面貌的獨特一隅,同時為我們在新時期如何進行傳統文化建設以及如何處理東西方文化關系等都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參考文獻:
[1] 黃興濤。文化怪杰辜鴻銘[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6:108-109。
[3] 黃興濤。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辜鴻銘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4] 唐慧麗。優雅的文明-辜鴻銘的人文理想新論[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9。
[5] 徐海燕,錢宏。辜鴻銘及其文化建設思想[J]。江西社會科學,2008(11):233。
[6]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J]。天津社會科學,2005(4)。
[7] 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19-20。
相關閱讀:大學生哲學文章在哪投稿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