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的游戲藝術(shù)
時間:2019年02月28日 分類: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摘要:米歇爾·德·塞托等學(xué)者從大眾的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創(chuàng)造,它是大眾規(guī)避技術(shù)、秩序控制的生活藝術(shù),這些創(chuàng)造日常生活的匿名者鮮為人知,在技術(shù)話語中沒有一席之地,然而我們可以在大眾日常生活中的行走、交往、飲食中發(fā)現(xiàn)這些隱微的創(chuàng)造。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善待大眾文化,那些看起來波瀾不驚的小動作,也是一種生活的藝術(shù)。
關(guān)鍵詞:大眾,日常生活實(shí)踐,米歇爾·德·塞托,游戲藝術(sh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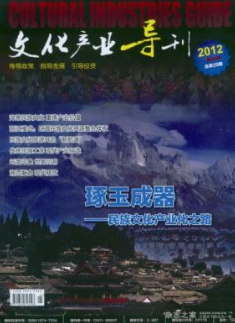
與法蘭克福學(xué)派等學(xué)派及學(xué)者將大眾日常生活視為逆來順受、毫無創(chuàng)建的對象不同,米歇爾·德·塞托等法國學(xué)者認(rèn)為大眾的日常生活是一種帶有藝術(shù)色彩的創(chuàng)造。塞托等法國學(xué)者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尋找被遮蔽的真相,他們思考的是社會中構(gòu)成文化的因素。
塞托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是文化產(chǎn)品的運(yùn)作,“文化本身并不是信息,而是根據(jù)目標(biāo)和社會關(guān)系制定的一系列活動的處理方式。”[1]335它不是“學(xué)者的文化”——塞托認(rèn)為這是一種被榮耀的光圈所遮蔽了的真相,也不是“大眾文化”——這是“御用文人從外部賦予的名稱”[2]7。
它是一種日常文化,與規(guī)則化、標(biāo)準(zhǔn)化模式下生存的大眾文化不同,“日常文化則一再以自己為表面對象,掩飾住了該文化中多種基礎(chǔ)的情境、特性和背景。”[1]336塞托等人關(guān)注的是一種匿名作者的創(chuàng)造,這是被邊緣化了的大眾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它逃離了權(quán)力規(guī)則的束縛,在被權(quán)力的觸須未曾觸及的細(xì)微空間中,塞托發(fā)現(xiàn)了那些巧妙的創(chuàng)造策略與戰(zhàn)術(shù)。塞托認(rèn)為在日常文化中,“秩序被藝術(shù)玩弄”[2]12。
一、日常生活中的大眾:創(chuàng)造的群體
塞托研究的對象不是作為社會原子的個體,而是社會群體,他肯定了大眾在文化消費(fèi)中的創(chuàng)造性,而不是蕭規(guī)曹隨與其它社會文化學(xué)者那樣將他們限定在一個被動的接受者位置上。大眾在文化生產(chǎn)系統(tǒng)中沒有立足之地,“生產(chǎn)系統(tǒng)……不再為‘消費(fèi)者’留有任何空間。”[2]33
然而在消費(fèi)中,存在著一種具有計謀的、四處分散著的另一種生產(chǎn)方式,這些運(yùn)作的形式多樣,它們與細(xì)節(jié)和機(jī)遇相關(guān),滲入生產(chǎn)機(jī)構(gòu)中,在經(jīng)濟(jì)秩序強(qiáng)加的產(chǎn)品的使用方式中來顯現(xiàn)出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與文化產(chǎn)品的消費(fèi)與社會背景和力量密切相關(guān),這使不同背景的消費(fèi)者具有不同的操作空間。
大眾消費(fèi)者的創(chuàng)造實(shí)踐“軌跡”超出了既定的社會陳述語言規(guī)則,他們在生產(chǎn)體系之外“勾勒出了有著其他興趣和愿望的計謀”[2]38,這種實(shí)踐“軌跡”是一種改寫,它是在“他者”的領(lǐng)域中作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場所。由于消費(fèi)者的創(chuàng)造“戰(zhàn)術(shù)”缺乏屬于自己專有的領(lǐng)地,因此他們的創(chuàng)造只能以碎片式的方式滲透到“他者”的領(lǐng)域中去,空間的缺乏,使消費(fèi)者更依賴于時間,他們需要“捕捉”時機(jī)。
消費(fèi)者作為弱勢群體,需要運(yùn)用戰(zhàn)術(shù)才能克敵制勝,戰(zhàn)勝生產(chǎn)體系,獲得自己的價值。匿名沉默的大眾日常生活實(shí)踐在具有特權(quán)的技術(shù)與哲學(xué)話語中找不到位置,在這些話語模式中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意義被遮蔽了。
科學(xué)話語是“社會—經(jīng)濟(jì)”秩序的話語,將社會地位與技術(shù)話語混淆起來,它的知識無法用來解釋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的那些計謀與花招。維特根斯坦通過對語言的研究從而使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那些無法言說(sagen)卻表現(xiàn)(zeigen)出來的發(fā)明被揭示出來,“語言的真相確定了歷史的真實(shí)性,超越了我們并將我們包裹在日常的模式之中。”[2]
62維特根斯坦使技術(shù)話語操縱的專屬地點(diǎn)被普遍性決定,它也是對日常語言的順應(yīng)。塞托在闡釋“信教者”從仿效伏都教的圣跡故事中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敘述空間時指出,“講述這門既得語言的方式將它變成了抵制的歌曲”[2]73,“信教者”沒有改變圣跡故事本身的清晰性與真實(shí)性,而是隱藏在既定秩序中對圣跡故事進(jìn)行了改編與創(chuàng)造。這些普通的大眾本身沒有在實(shí)踐過程中得到展現(xiàn),他們的創(chuàng)造是通過文本展現(xiàn)出來的。
對文化產(chǎn)品的使用方式形成了對其生產(chǎn)體系的抵制作用,在這種抵制過程中顯現(xiàn)出大眾花樣繁多的“智慧”,它們具有挫敗他者——也就是約束大眾的體系、規(guī)則的——建構(gòu)的空間的力量。故事、傳說、游戲中提供了大眾能夠創(chuàng)造的話語空間,“這些故事賦予了偽裝/隱瞞以特權(quán)。……確保出生卑微的人在神奇、虛幻的空間中取得勝利。這個空間保護(hù)了弱者的武器,使它們免于既定秩序的真相。”[2]80那些用以抵制秩序原本被科學(xué)理性所消除的計謀、變動在“花招”的作用下被運(yùn)用到日常語言中,并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得以實(shí)踐。
塞托認(rèn)為,大眾日常文化模式不局限于過去、農(nóng)村、原始人身上,它存在于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中心。大眾在既定秩序中如魚得水般運(yùn)用計謀來進(jìn)行著創(chuàng)造,他們改變著事物的有效秩序。大眾日常文化并非外在于既定秩序外的實(shí)體,它就存在于既定秩序中,是對既定秩序的“藝術(shù)玩弄”。
二、都市行走:空間創(chuàng)造
都市行走者擺脫了既定秩序的監(jiān)管與排斥,在日常生活中諸如都市行走等微觀實(shí)踐中發(fā)揮著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并將這些創(chuàng)造性活動滲透到社會監(jiān)管的網(wǎng)絡(luò)之中。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到米歇爾·福柯對于監(jiān)獄及學(xué)校等領(lǐng)域的研究。福柯從細(xì)節(jié)中論述了權(quán)力的運(yùn)作機(jī)制。這個研究思路無疑也啟發(fā)了塞托等人的研究,他們也遵循了從細(xì)節(jié)處來研究都市行走者對秩序的巧妙回避及在這一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林林總總的技巧方式,“腳步游戲是對空間的加工”[2]174。
這種步行的游戲無法被記錄,它的時間性也沒有得到體現(xiàn),唯一表現(xiàn)出來的是作為固定下來的路線。換言之,其創(chuàng)造性無法被記錄捕捉。都市空間是行走者活動的產(chǎn)物,充滿互相沖突的程序,它是被實(shí)踐的地點(diǎn)。代表著權(quán)力與規(guī)則的地點(diǎn)被人們的實(shí)踐轉(zhuǎn)換成了空間,空間缺少地點(diǎn)那樣的“專屬”與穩(wěn)定性,它是變化著的。梅洛—龐蒂將都市行走者實(shí)踐的空間與“幾何”空間區(qū)分開來,他認(rèn)為前者與存在經(jīng)驗聯(lián)系在一起。
“地點(diǎn)”與實(shí)踐“空間”之間的區(qū)分是,前者缺乏時間性,它只是一些冷冰冰的物,后者具有時間性,它表現(xiàn)為使物具有歷史性。都市行走者的行走實(shí)踐構(gòu)建著一種現(xiàn)時性的關(guān)系,它使其他人的活動也能參與進(jìn)來。“地點(diǎn)”與實(shí)踐“空間”二者之間可以轉(zhuǎn)換,即缺乏時間性的地點(diǎn)可以在實(shí)踐的作用下變成具有歷史性的存在,“讓沒有生命的物品……復(fù)活,……屬于它們自己的空間”[2]201。
走路行為對城市體系而言,如同陳述行為(speechact)對應(yīng)于語言或者被陳述之物[2]174。走路行為包含著適應(yīng)地形體系、對地點(diǎn)的空間適應(yīng)過程、位置關(guān)系等“陳述”功能。步行者的“陳述”改變著空間系統(tǒng),后者是一種秩序,具有限制性,它是規(guī)劃者與建筑師所安排的空間,類同于語法學(xué)家和語言學(xué)家創(chuàng)造的“本義”,這是一種標(biāo)準(zhǔn)。步行者在空間能指中進(jìn)行著挑選,或者通過游戲改變著它們的使用方式,或者根據(jù)自己的意愿不按部就班于空間能指,而是任意在這些代表著秩序的地點(diǎn)——“一個地點(diǎn)就是一種秩序”[2]199——之間進(jìn)行組織,建構(gòu)出新的空間“表達(dá)方式”。
都市步行者以兩種呼應(yīng)的修辭在空間能指中進(jìn)行著創(chuàng)造:“提喻”與“連詞省略”,前者是以部分代替整體——比如人們以某一櫥窗中的待售自行車來指代街區(qū),后者是取消了地點(diǎn)之間的連續(xù)性與因果性——人們會有意忽略某些地點(diǎn)。這樣一來,被行走者實(shí)踐過的都市空間能指,就形成了新的空間句法,這種句法包含著“夸大的個性與分散的小群島”,都市空間的連續(xù)性與整體性被“具有神話結(jié)構(gòu)的路段取代了”[2]179。步行者的行走對這些空間秩序進(jìn)行改造,既使他們顯現(xiàn),又改造著它們,“因為步行過程中的橫穿、改道、或者即興發(fā)揮等行為青睞、改變或者拋棄了基本的空間元素。……步行者將每一個空間能指變成了其他的東西。”[2]175
都市行走使地點(diǎn)這一象征著權(quán)力與規(guī)則的對象變得缺失,而步行者之間相互交織的行走形成了新的陳述。由于行走者是“匿名”者,他們的行為不能被都市文本所記錄,它們是“反文本”——對既定秩序與能指的背離。
三、都市居住:交往藝術(shù)
都市生活是一種“共存的藝術(shù)”[1]25,人們通過禮儀而互相妥協(xié),放棄自己的無秩序沖動,服從于集體生活。人們在對共同契約的遵守中獲得周圍人的“認(rèn)可”“考慮”,這是日常生活實(shí)現(xiàn)的前提。居住者在都市中的行為成為社會符號網(wǎng)絡(luò)的一部分,這些社會符號約束著人們在住處與工作、熟悉與陌生、男女性之間的交往關(guān)系。
在居住區(qū)內(nèi),居住者會在周邊的地點(diǎn)進(jìn)行購置日常用品、與鄰居打交道等活動,這些交往常常帶有事先無法預(yù)料的偶然性,即便如此,人們還是使這種交往保持在社會規(guī)范內(nèi),換言之,偶然性中暗含著必然性。這種規(guī)范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平衡,既不能因為“走”得太近而引起彼此之間的尷尬,也不能因為離得太遠(yuǎn)而疏遠(yuǎn)鄰里之間的關(guān)系。
居住區(qū)內(nèi)的規(guī)范起著標(biāo)準(zhǔn)化的排斥作用,即那些符合規(guī)范的人會得到肯定,而那些不符合規(guī)范的“怪人”則會被排除出去。標(biāo)準(zhǔn)化的結(jié)果是確保大家在居住區(qū)內(nèi)和平共存。人們努力使自己的行為與這個價值、行為系統(tǒng)一致,仿佛帶著面具扮演某種角色。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是預(yù)先被這個系統(tǒng)設(shè)定好了的,一旦置身于這個系統(tǒng)中,人們的行為就好像是透明的,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是可以被解讀的,“……這些動作……身體是一塊寫上了字的黑板——因此是能被解讀的”[1]35。那種標(biāo)榜自我,違背了中立原則(中庸之道)的特立獨(dú)行行為是不為居住區(qū)所容忍的。
然而,這并非說,人們只能在規(guī)則面前馬首是瞻,毫無自我,在居住區(qū),違背一般規(guī)則的行為可以在私人空間中才能進(jìn)行。這需要一定的技巧,因為禮儀對居住區(qū)的各個角落事無巨細(xì)地進(jìn)行著“審查”,防止居住區(qū)無法預(yù)料事件的發(fā)生,“以禮儀為尺度來衡量一切”[1]38。
這種權(quán)力運(yùn)行的機(jī)制非常類似于福柯在《性經(jīng)驗史》中提及的權(quán)力模式,按照福柯的描述,在宗教等權(quán)力的壓制下,性話語不僅沒有變得萎縮,反而更豐富了,因為權(quán)力不斷誘使人們說出潛在的欲望,從而不斷使那些隱蔽的內(nèi)容暴露出來,以達(dá)到進(jìn)一步對人的控制,在這一過程中相生相成的是性話語的不斷豐富,“權(quán)力機(jī)構(gòu)煽動人們?nèi)フ勑裕⑶艺劦糜嘤?hellip;…性落入了話語的掌握之中”[3]。
都市居住者在遵循規(guī)則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自己喜好的生活,“主體根據(jù)自身的需要……打破了城市機(jī)制的限制”[1]30。比如,人們可以使用雙關(guān)語來回避禮儀的束縛,一些被認(rèn)為是不雅的“色情”語言借助于雙關(guān)語能夠得以重見天日,因為性言論常常帶有模棱兩可性,它無法被準(zhǔn)確陳述出來,因而可以獲得禮儀的接受。這種接受也是有條件的,色情的話題是個別進(jìn)行的,而且要注意語調(diào)與表情及對象(孩子、老人面前不允許談?wù)撨@些話題)。
這是一種巧妙回避規(guī)則的花招,“用計謀戰(zhàn)勝禮儀”[1]48這種玩笑在居住區(qū)的菜市場中會表現(xiàn)得比較普遍,因為菜市場中的商販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處在一種復(fù)雜社會關(guān)系中,難以在禮儀方面做到分毫不差。其次,商販們處于更替輪換的位置上,他們與顧客之間并沒有一種穩(wěn)定關(guān)系,因為禮儀也無法約束他們。
此外,手勢也會代替語言,以含蓄的方式來表現(xiàn)自己的動機(jī)與欲望。不管是雙關(guān)語也好,手勢也好,它們都發(fā)揮著由此及彼的引申作用,是對既有規(guī)則(語言與行為規(guī)范)的破壞與沖擊。這種日常生活的實(shí)踐藝術(shù)“打破日常生活最深處的平庸”[1]54。
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對此秘響旁通,似乎可以作出某種解釋。在《西湖夢》中,余秋雨視文人士大夫與青樓歌伎為對峙的兩種生命力,前者看不慣世俗的爾虞我詐而躲進(jìn)孤山成一統(tǒng),比如林和靖。這種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固然令人稱道,然而封閉的生活也導(dǎo)致了生命力的枯萎,他們對抽象道德律令的實(shí)踐使人生變成了文化標(biāo)簽。另一種人生雖然“野潑潑”卻充滿生氣,如蘇小小。
蘇小小之所以數(shù)百年來為人們樂道與憑吊,是因為她自由無拘束的生命意志,“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4]日常生活中的實(shí)踐藝術(shù)包含著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它同樣是受沖動支配的……強(qiáng)大力量”[1]54。這種思想似乎是對尼采生命哲學(xué)的承繼,尼采認(rèn)為理性扼殺人的本能力量,因此他對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口誅筆伐,而推崇象征著人的生命力的酒神沖動與日神沖動,“兩種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并存,……相互不斷地激發(fā)更有力的新生”[5]。
四、日常飲食:味覺藝術(shù)
布爾迪爾將人們的行為與固化的階層捆綁在一起,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與社會位置息息相關(guān)。在這種闡釋模式下,“一個群體或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已經(jīng)預(yù)先被否認(rèn)了”[1]241,似乎沒有什么新東西可以進(jìn)入人們的生活,像飲食實(shí)踐被認(rèn)為是沿襲故舊的行為,它與人們的童年記憶、母親的烹飪風(fēng)格緊密關(guān)聯(lián)。
布爾迪厄沒有看到人們對食物的消費(fèi)方式中包含著一種創(chuàng)造——或者說他只是模糊意識到了。人們在食物的消費(fèi)與選擇中既構(gòu)成了各種秩序,也在背離著秩序,“……食物成了各種有秩序或反秩序的分層靜悄悄發(fā)生的場所”[1]245。它受時間、地點(diǎn)、群體、個人的多種創(chuàng)造及各種無法預(yù)測的偶發(fā)小事件的影響。選擇食材的過程不斷更新著人們的經(jīng)驗與能力。
人們在市場中鑒別食材的時候,“伸出食指輕觸水果來辨別其成熟程度、用拇指感覺紅皮蘿卜是否硬實(shí),眼睛謹(jǐn)慎地一掃就能發(fā)現(xiàn)蘋果表面的斑點(diǎn)……在此過程中,人們更新了自己的能力”[1]273。在超級市場中,對貼滿標(biāo)簽的食品,人們購買的過程中通過對標(biāo)簽的辨別、比較、檢查來去蕪存菁,挑選到自己最滿意的食品。
在過去的市場中購物,人們需要立足于自己的經(jīng)驗知識,不能讓商販的言語影響自己的判斷,而現(xiàn)在,購買者要走出自己的經(jīng)驗知識,學(xué)會從標(biāo)簽中去發(fā)現(xiàn)通向良好品質(zhì)食品的途徑。人們對食物配料的審視、配料的組合及其在烹飪中的作用等因素就可以組成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多種詞條組合目錄。
因此,無法使用某種固定的方式來編定這種餐飲目錄,它是變化多端,難以窮盡的。比如一種植物食材,它就可以在是否人工種植、土壤的質(zhì)地、天氣、種子的良莠等方面做出區(qū)分。因此,一種食物的制作只需在配料上稍稍做出改變就變成新的作品,它無法以既定的語言來描述。烹飪也是一個自由創(chuàng)造的過程,“烹飪既是一項智力活動也是一項體力活動;做這件事需要調(diào)動所有的智慧和記憶。
做飯的人必須組織、決定、準(zhǔn)備,還得默記、適應(yīng)、改變、發(fā)明、組合”[1]267。做飯的人需要控制好時間、購買食物的價格,還能即興發(fā)揮,彌補(bǔ)準(zhǔn)備的不足或操作上的失誤;對臨時來訪的客人需要準(zhǔn)備足夠的飯菜,還得避免讓再次來訪的客人吃同樣的食物。對家庭主婦而言,烹飪需要自由的創(chuàng)造能力,雖然操持的是鍋碗瓢盆的事情,她們并不顯得千人一面,而是各有千秋,在生活實(shí)踐中,“她們的烹飪風(fēng)格固定了,品味開始顯露出特色,想象力得到了解放……她們玩著巧妙的游戲”[1]268。
在家庭中,母親出于孩子健康的考慮,總會竭盡所能讓他們的膳食合理,然而這并不能令孩子們感到滿意,他們發(fā)明了成千上萬種對付母親的花招:在外面肆無忌憚地吃東西、在母親面前有意贊美別人家的食物美味。對于各種現(xiàn)代科技進(jìn)入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shí),研究者也表現(xiàn)出了擔(dān)憂,因為這些電器似乎又使人們回到了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的窠臼中去。
人們以前的主動性被服從于機(jī)器的被動性取而代之,家庭主婦們感到雙重缺失“她失去了自己的經(jīng)驗知識(與過去相比),也不比機(jī)器方面的理論和科學(xué)技術(shù)知識(和現(xiàn)在相比)”[1]280。而在過去,她們在廚房中儼然就是揮灑自如的創(chuàng)造者與發(fā)明家,隨心所欲地修改著規(guī)則與制定出新的法則,那里面透出她對自己能力的驕傲,在食材面前,主婦們以臂使指仿佛在指揮自己的“士兵”。而如今,現(xiàn)代電器在廚房中擔(dān)任起來主角,現(xiàn)代分工模式進(jìn)入了生活中,標(biāo)準(zhǔn)化的運(yùn)作使家庭主婦們感到單調(diào)、陰郁、空虛。研究者們對此頗感憂慮,“我們能夠只保留一種物質(zhì)文化的優(yōu)點(diǎn)而去掉它的缺點(diǎn)嗎?在舊和新之間,有沒有可能產(chǎn)生一種圓滿的結(jié)合呢?
現(xiàn)在對于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核心問題,但是我們還不能提供答案。”[1]281研究者們認(rèn)為現(xiàn)代工業(yè)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人們的創(chuàng)造性,它不能使人感到幸福,而在廚房等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人們通過自己的雙手的勞作創(chuàng)造的私人生活空間“我們可以感到一種深切的快樂。”[1]281這與梁漱溟所說的“個人為自由之主體”[6]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對技術(shù)的憂思是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社會—文化”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diǎn),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中包含著對技術(shù)擴(kuò)張的擔(dān)心;霍克海姆與阿道爾諾在論及現(xiàn)代性時就指出:“個體在他使用的機(jī)器面前消失不見了。”[7]人在工業(yè)社會中被物化了,拜物教擴(kuò)散到人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丹尼爾·貝爾認(rèn)為機(jī)器改變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世界變得技術(shù)化,機(jī)器占統(tǒng)治地位,“人被當(dāng)做物來對待”[8]。喬治·西美爾指出貨幣作為一種聯(lián)系人們生活的紐帶水銀瀉地一般在各方面發(fā)揮著作用,它將情感排除在外,人們的生活“具有嚴(yán)格的因果性,……它與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宇宙很類似”[9]。
這里的金錢帶有現(xiàn)代色彩,作為一種隱喻,金錢與工業(yè)技術(shù)具有某種類似性,即二者都在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剝奪了人們對于生活的主導(dǎo)性,變得屈從。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shù)》中指出,人與動物的區(qū)別在與前者對環(huán)境并非機(jī)械被動的反應(yīng),他們具有改變環(huán)境的自由,“……人的性格生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從機(jī)械律的”[10],走出機(jī)械控制宿命的道路,大概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進(jìn)行審美創(chuàng)造,“審美……保持對強(qiáng)權(quán)的對抗(某種模式、系統(tǒng)或秩序的強(qiáng)權(quán))”[1]335。
五、結(jié)語
大眾在一系列社會、歷史日常生活敘事中似乎沒有多少意義與創(chuàng)造性可言。波德里亞在《消費(fèi)社會》中指出豐盛的物質(zhì)社會如同一個巨大的網(wǎng)絡(luò),人們身處由物質(zhì)構(gòu)成的符號系統(tǒng)中,如進(jìn)迷宮,“我們處在‘消費(fèi)’控制著整個生活的境地”[11]。列斐伏爾就認(rèn)為:“生產(chǎn)這個概念被縮小使它與日常生活靠得更近,因此它變得平庸。”[12]BenHighmore指出,“日常生活”在西方文化中具有二元性,其中一個方面是:“(日常生活:筆者注)最為重復(fù)的行為、最常見的旅行、最稠密的生活空間填充著日復(fù)一日的內(nèi)容。從價值與品質(zhì)來衡量日常生活:它是平淡無奇的。最稠密的居住空間形同監(jiān)獄,重復(fù)的動作是沉重的規(guī)范。它特別的質(zhì)素是缺少優(yōu)點(diǎn)。”[13]
大眾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具有某些系統(tǒng)性與靈活性,是規(guī)則、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之外的某種自成一體的創(chuàng)造,“它是一種靈活的與延續(xù)的集體,用無法扯破與編制的碎片編織成一個緊密的結(jié)構(gòu),大量失去名字與面孔的英雄如同變成街道上編碼的河流,一種可計算的變化語言與合理性并不屬于任何人。”[14]他們無處不在,其創(chuàng)造無法被賦予名字與身份,然而他們是在改變著乏善可陳的日常生活,將它改造成一種具有藝術(shù)色彩的內(nèi)容。
這啟示我們,走出精英立場與視角去審視大眾的日常文化與實(shí)踐,在“技術(shù)—哲學(xué)”話語的文本中,我們無法發(fā)現(xiàn)這一具有顛覆性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如果忽視這些,僅僅以“技術(shù)—哲學(xué)”話語作為認(rèn)識生活的全部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我們必須拾遺補(bǔ)缺,填補(bǔ)這一空白。從國內(nèi)文化研究的現(xiàn)狀來看,雖然認(rèn)識到了大眾日常生活文化的價值,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的三足鼎立表明了這種認(rèn)識對大眾日常文化的認(rèn)可,但目前的研究僅在宏觀上,還缺乏微觀意義上的研究方法,塞托等學(xué)者對大眾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研究對我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網(wǎng)絡(luò)文化便是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方面,網(wǎng)絡(luò)上,無數(shù)無名的作者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顯現(xiàn)出自己的存在與智慧,然而這些片言只語的段子難以登大雅之堂,但它們豐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在會心一笑之余也有所思。如最近在網(wǎng)絡(luò)上出現(xiàn)一句流行語“主要看氣質(zhì)”,新京報將其解讀為“無聊”[15]。然而很多網(wǎng)友能從中自得其樂,笑料段子百出,令人捧腹。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在創(chuàng)造著日常生活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塞托,賈爾,梅約爾.日常生活實(shí)踐2.居住與烹飪[M].冷碧瑩,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
[2]塞托.日常生活實(shí)踐1.實(shí)踐的藝術(shù)[M].方琳琳,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3]福柯.性經(jīng)驗史[M].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13.
[4]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151.
[5]尼采.悲劇的誕生[M].周國平,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2.
[6]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yùn)[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2.
[7]霍克海姆,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xué)片段[M].渠敬東,曹衛(wèi)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前言3.
[8]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嚴(yán)蓓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56.
[9]西美爾.金錢、性別、現(xiàn)代生活風(fēng)格[M].顧仁明,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5:21.
文學(xué)方向期刊推薦:《文化產(chǎn)業(yè)導(dǎo)刊》(月刊)創(chuàng)刊于2010年1月,是中國人民大學(xué)和中國政法大學(xué)兩大社科名校聯(lián)袂打造的我國第一家服務(wù)于文化產(chǎn)業(yè)的行業(yè)雜志。 《文化產(chǎn)業(yè)導(dǎo)刊》讀者定位:各級黨和政府相關(guān)部門,高校和科研機(jī)構(gòu)的相關(guān)領(lǐng)域研究人員,文化產(chǎn)業(yè)各領(lǐng)域高層管理者以及有志于文化產(chǎn)業(yè)投資的各類投資家和專業(yè)人士。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fù)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fù)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yī)學(xué)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yè)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qū)和影響
- 2025-02-10經(jīng)管專業(yè)快速發(fā)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fā)論文,解答及指導(dǎo)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fā)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shù)據(jù)庫?scopus數(shù)據(jù)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fù)合材料科學(xué)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jié)能領(lǐng)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shù)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xiàn)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fā)表的論文文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