Փ����l(f��)չ��(qu��n)���w�Ă�(g��)��
�r(sh��)�g��2019��11��18�� ����ČW(xu��)Փ�� �Δ�(sh��)��
����ժҪ:��������Լ��w�˙�(qu��n)��ʽ���F(xi��n)�İl(f��)չ��(qu��n)�������w�Ƿ������(g��)���Լ���(g��)�������е����w��λ���}�����о��l(f��)չ��(qu��n)��(y��ng)��(d��ng)��Q�Ć��}���l(f��)չ��(qu��n)����һ�(xi��ng)���w�˙�(qu��n)��Ҳ��һ�(xi��ng)��(g��)���˙�(qu��n)����(g��)������l(f��)չ��(qu��n)�����w�����(qu��n)����(sh��)�F(xi��n)�ܵ����A�ӡ��Ԅe�������ȸ��������ص�Ӱ���
�����P(gu��n)�I�~:��(g��)��;���w;�l(f��)չ��(qu��n);���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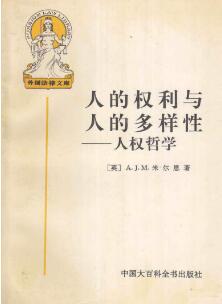
����һ����(g��)������l(f��)չ��(qu��n)���w�ķ��ɵ�λ
������(g��)���ǰl(f��)չ��(qu��n)�����w���䷨�ɵ�λ��W(xu��)�g(sh��)��Փ�����J(r��n)ͬ�������@һ�J(r��n)֪�����ԏ������ϼ����������������
����(һ)��(g��)���c���w�P(gu��n)ϵ����Փ�J(r��n)�R(sh��)
�������������˙�(qu��n)��Փ�У��Խ����Y�a(ch��n)�A��(j��)�����\(y��n)��(d��ng)�_ʼ�����������˙�(qu��n)����һֱ���Ԃ�(g��)���˙�(qu��n)�����w�ģ����������(hu��)�Ļ����y(t��ng)Ҳ���ӏ�(qi��ng)�{(di��o)��(g��)�w�����(hu��)�е����ú̓r(ji��)ֵ�����������W(xu��)�ߺ���J(r��n)�飬“�����˵Ă�(g��)�˙�(qu��n)������Ȼ�ġ����еę�(qu��n)��;�������ǁ��������(hu��)���κ�������ٛ(z��ng)�c���������ǁ��ԑ���;���������ڑ��������ڵġ�”[1]369���ô�W(xu��)�s��·�h���R�J(r��n)�飬“�˙�(qu��n)�@��(g��)�~�H�Hָ���������˵Č��Զ����еĂ�(g��)�˙�(qu��n)�������ɡ�”[2]12
���������o(j��)90��������@���H���(hu��)�����w�˙�(qu��n)�͂�(g��)���˙�(qu��n)�����P(gu��n)ϵ���|(zh��)���c��Փ���W(xu��)��ӑՓ���ң����д����Ե�����ƵȌW(xu��)�ߡ�
������ƽ��ڏ�(qi��ng)�{(di��o)���w�˙�(qu��n)�͂�(g��)���˙�(qu��n)֮�g�Ľy(t��ng)һ�Ժ�һ���ԣ��J(r��n)�錦���@�ɷN��͵��˙�(qu��n)��Ҫ����ͬ�ӵ���ҕ�c���o(h��)��“�����v����֮���ķN��(qu��n)������Ҫ��Ҳ���ˏ�(qi��ng)�{(di��o)����֮���ķN��(qu��n)���Ӵ��c��λ���ߡ�”[5]��?y��n)��ڷ����ϣ������ԙ?qu��n)�����w�Ĵ�С�ߵ́��_����(qu��n)���ĵȼ�(j��)�Լ������o(h��)�ĵ�λ�����w�˙�(qu��n)��ijһ�Ƕȁ�����Ҳ�ǂ�(g��)���˙�(qu��n)�����l(f��)չ��(qu��n)�e����ָ���l(f��)չ��(qu��n)����һ�(xi��ng)���ҵļ��w�˙�(qu��n)����Ҫָ�������Ї��Ҷ����е�ƽ�Ȱl(f��)չ�ę�(qu��n)��;�l(f��)չ��(qu��n)����һ�(xi��ng)��(g��)���˙�(qu��n)���tָ����ÿ��(g��)�˶���(y��ng)�ɞ�“�l(f��)չ��(qu��n)���ķe�O���c�ߺ�������”[5]��
�����M��Փ���ĽǶȲ��M��ͬ�����Ѓ��c(di��n)��һ�µġ�һ�Ǽ��w�˙�(qu��n)�c��(g��)���˙�(qu��n)���˙�(qu��n)�ăɷN�ΑB(t��i)���l(f��)չ��(qu��n)���Ǽ��w�˙�(qu��n)�͂�(g��)���˙�(qu��n)����Ĵ��������Dz��ˏăr(ji��)ֵ����팦���w�˙�(qu��n)�͂�(g��)���˙�(qu��n)�������p���ص��Д࣬�J(r��n)��“���w�˙�(qu��n)���ڂ�(g��)���˙�(qu��n)”������“��(g��)���˙�(qu��n)���ڼ��w�˙�(qu��n)”���^�c(di��n)����Ƭ��ġ����˙�(qu��n)���w�M(j��n)�л����ķ����������ڌ��l(f��)չ��(qu��n)�����w���M(j��n)һ����̽ӑ���䌍(sh��)���S���r(sh��)���İl(f��)չ���Լ��l(f��)չ��(qu��n)����Ă�������Փ�о������M(j��n)���l(f��)չ��(qu��n)���Ǽ��w�˙�(qu��n)��Ҳ�ǂ�(g��)���˙�(qu��n)���^�c(di��n)�ڇ��H���(hu��)�ϵõ���Խ��Խ��ć��ҵ��J(r��n)ͬ��
�������ȣ������P(gu��n)�ć��H�ļ�������1986��(li��n)�χ����l(f��)չ��(qu��n)�����ԡ���Մ�������@һ�l(f��)չ��(qu��n)���w��ͬ�r(sh��)��������(g��)���@һ�l(f��)չ��(qu��n)���w�����磬��(qi��ng)�{(di��o)�l(f��)չ��Ŀ����������������Ђ�(g��)�˷e�O���c�l(f��)չ���������������棬�Ը���������������Ђ�(g��)�˵ĸ���;��(qi��ng)�{(di��o)�l(f��)չ�C(j��)��(hu��)�����LJ����Լ��M�ɇ��ҵĂ�(g��)�˵�һ�(xi��ng)���Й�(qu��n)��;���J(r��n)��(chu��ng)�������ڸ�������͂�(g��)�˰l(f��)չ�ėl���LJ��ҵ���Ҫ؟(z��)�εȵȡ���Σ��ČW(xu��)���Ͽ���ӑՓ�l(f��)չ��(qu��n)�����w�ǂ�(g��)��߀�Ǽ��w��߀��Ҫ���傀(g��)���˙�(qu��n)�c���w�˙�(qu��n)֮�g���P(gu��n)ϵ����(g��)���˙�(qu��n)�c���w�˙�(qu��n)����֮�g����������(li��n)ϵ��
������(g��)���˙�(qu��n)�Ǽ��w�˙�(qu��n)�Ļ��A(ch��)�����w�˙�(qu��n)�t�����ڼӏ�(qi��ng)��(g��)���˙�(qu��n)�ı��ϡ���(g��)���c���w��������(y��ng)�ģ������(li��n)ϵ�ġ���(g��)���ǽM�ɼ��w�Ă�(g��)�ˣ����w���ɂ�(g��)�˽M�ɵļ��w������֮�g�����Ͳ��ɷָ�ٴΣ��İl(f��)չ��(qu��n)�a(ch��n)���Ěvʷ�^�́������l(f��)չ��(qu��n)���ȳ��F(xi��n)�ڇ��H���I(l��ng)�������ԛQ��(qu��n)����ƽ��(qu��n)���h(hu��n)����(qu��n)�ș�(qu��n)��һ�ӣ����ɏV��İl(f��)չ�Ї����ڷ��ۡ���ֳ�������^�����Լ��w�˙�(qu��n)����ʽ��ȡ���a(ch��n)���ġ�����ƽ��������ġ��˙�(qu��n)���W(xu��)���̲��У��J(r��n)��l(f��)չ��(qu��n)����һ�(xi��ng)“���ҙ�(qu��n)��”�������w�˙�(qu��n)����������x��:“�����ϵ��κ�һ��(g��)���ң���������Щ�l(f��)չ�Ї���(�������������)����ͬ��������‘�l(f��)չ�C(j��)��(hu��)����’�ę�(qu��n)������Ҫ������(g��)���H���(hu��)�����Ї��ң���������Щ�l(f��)�_(d��)���ң���(y��ng)�ڇ��Hһ��(j��)��ȡ���ߵġ������ġ������ļ�������ʩ�������@һ��(qu��n)���Č�(sh��)�F(xi��n)��”[7]
����49��ˣ��ڇ��H���I(l��ng)�l(f��)չ��(qu��n)����һ�(xi��ng)���w�˙�(qu��n)�����ԇ��������(qu��n)�����w�ġ����l(f��)չ��(qu��n)���邀(g��)���˙�(qu��n)����Ҫ�Ǐć���(n��i)���I(l��ng)������]�ģ���������x�LJ��ґ�(y��ng)��(d��ng)��ȡ�e�O�Ĵ�ʩ�팍(sh��)�F(xi��n)����İl(f��)չ��(qu��n)�����_�������˰l(f��)չ�C(j��)��(hu��)���ȣ����ܫ@�ý������͘I(y��)��ס�����t(y��)���ȸ�������YԴ���M�ܰl(f��)չ��(qu��n)���Լ��w�˙�(qu��n)����ʽ���F(xi��n)�ģ������S���J(r��n)�R(sh��)������ġ��l(f��)չ��(qu��n)�����ԡ��ı����Ϳ��Կ��������U(ku��)չ����(g��)�˲�������(g��)���ڃ�(n��i)��
����(��)��(g��)���c���w���P(gu��n)ϵ�Č�(sh��)�H��r
�����l(f��)չ��(qu��n)���w��(d��ng)�еļ��w�͂�(g��)�ˣ����ߛ]����ȫ�^���Ľ��ޣ���ʹ�����鼯�w��ʽ�İl(f��)չ��(qu��n)��Ҳ������ȫ�dz���ĸ�����ę�(qu��n)���V��(sh��)�F(xi��n);��Ҳ�Ǿ��w�ģ�����Ҫ���w��ÿһ��(g��)��(g��)�w���l(f��)�]���^�܄�(d��ng)�ԣ��e�O���c�l(f��)չ���^�̡���(g��)�˰l(f��)չ��(qu��n)�Ĵ��������˵Ă�(g��)�w���c���w�Ԡ�r�������(j��)�ġ�
�������ȣ������Ԃ�(g��)�w��B(t��i)���ڵġ��R��˼����(j��ng)�f�^:“�κ���vʷ�ĵ�һ��(g��)ǰ��o�����������Ă�(g��)�˵Ĵ��ڡ�”[8]23���܌W(xu��)�����ϣ��˿��Է֞邀(g��)�w�����Լ�������ˡ�������ˣ���һ��(g��)�߶ȳ���ĸ��ָ��������(g��)������(hu��)�����ɟo��(sh��)��(g��)��(g��)�w�������M�ɵġ����邀(g��)�w�����c������˵İl(f��)չҎ(gu��)�ɲ���ȫ��ͬ��������(hu��)�Įa(ch��n)�����l(f��)չ�������������L�Ěvʷ��
��������ÿһ��(g��)�ˣ����������Ă�(g��)�w���ڣ��sֻ�ж̶̵Ď�ʮ�꣬���һ�ٶ���Ĵ��m(x��)�r(sh��)�g������^������(hu��)���f��ÿһ��(g��)��(g��)�w�Ĵ��ڶ����^��һ��(g��)��(x��)��Ƭ�Σ�����ÿһ��(g��)��(g��)�w�Ĵ��ڶ���������ăr(ji��)ֵ�����x����?y��n)�������˵İl(f��)չ��KҪͨ�^һ��(g��)��(g��)��(g��)�w�İl(f��)չ���w�F(xi��n)���ڷ��ɸ����ϣ����������܉����ܙ�(qu��n)�����Г�(d��n)�x��(w��)�����w�����ڡ���(qu��n)����K���ж���(hu��)�Ǿ��w�ģ���ʹ�����鼯�w�ę�(qu��n)����Ҳ�кܶ���w��Ҏ(gu��)������K߀��Ҫ�䌍(sh��)��һ��(g��)��(g��)�܉����Й�(qu��n)���������x��(w��)�Ă�(g��)�w���ϡ�
������Σ������Ԃ�(g��)�w��B(t��i)�l(f��)չ�ġ���Ěvʷ“ʼ�Kֻ�������Ă�(g��)�w�l(f��)չ�Ěvʷ”[9]478��������(hu��)�İl(f��)չ�ǟo�ģ���������ÿһ��(g��)�F(xi��n)��(sh��)�ġ����w���ˁ��f����l(f��)չ�����ģ��Ҿ���һ���Ŀ��^Ҏ(gu��)�ɡ����邀(g��)�w��B(t��i)���ڵ��ˣ�һ��֮��Ҫ��(j��ng)�^�냺���׃������ꡢ���ꡢ���ꡢ�����@�ׂ�(g��)�A�Ρ��������ċ냺��ֻ������������(g��)�w�����ڣ����w���������������պ�ij��L�Լ����(hu��)�����в���l(f��)չ�ġ�
�������邀(g��)�w���˵İl(f��)չ�^�̣���һ��(g��)����Ȼ���D(zhu��n)�����(hu��)�ˣ��ڲ������������Ļ��A(ch��)�ϣ���(sh��)�F(xi��n)�䝓�ڿ����Ե��^�̡����@��(g��)�^���У���ʼ�K���Ԃ�(g��)�w�Ġ�B(t��i)�l(f��)չ����������W(xu��)�����İ���·�m�������f��“�˱�횪�(d��)�Ե��������Լ�”[10]17��“���ԇ�D�����Լ���Ŭ����Q���nj����Լ��Ć��}�������H���ܶ��ұ���Є�(chu��ng)���ԡ���(chu��ng)���ԛQ���������ٔ�(sh��)�˵��ٔ�(sh��)���(d��ng)��������һ�N��Ȼ��ֲ�����˱����Ĵ��ڽY(ji��)��(g��u)�С�”[10]17��
��������w�ǂ�(g��)�w�Y(ji��)�ϵĮa(ch��n)����w�Ǿ���ij�N��ͬ���Ե�һ��˵ļ��ϣ����ɂ�(g��)�w�Y(ji��)�϶��ɵģ���(g��)�w�ǘ�(g��u)�ɼ��w������ġ���С��Ԫ�ء����w�ı��F(xi��n)��ʽ�����LJ��ҡ����壬�����Ǿ���ij�N���ܵ����(hu��)�M�����mȻ��(g��)�w�ǘ�(g��u)�ɼ��w����СԪ�أ����nj����κ�һ��(g��)���w���f������횳��J(r��n)��(g��)�w�Ĵ��ڣ������ɺ�ҕ��(g��)�w�ăr(ji��)ֵ����?y��n)�ʧȥ��(g��)�w�����w��ʧȥ�˸��������ˣ��R��˼�eָ����“��(y��ng)��(d��ng)�������°�‘���(hu��)’��(d��ng)������Ė|��ͬ��(g��)�ˌ�����������(g��)�������(hu��)�����”[11]122
������ˣ�ֻ�г���{(di��o)��(d��ng)���w��ÿһ��(g��)��(g��)�w�����c�l(f��)չ���������w���Ƅ�(d��ng)���w�İl(f��)չ��ͬ�r(sh��)����(g��)�w�İl(f��)չ����Ó�x�ڼ��w����(sh��)�F(xi��n)��ֻ�м��w�l(f��)չ�ˣ����ܞ鼯�w�е�ÿһ��(g��)��(g��)�w��(chu��ng)����õĭh(hu��n)���c�l������(sh��)�F(xi��n)��(g��)�w�����İl(f��)չ�����ԣ���Փ�LJ��ҵİl(f��)չ��(qu��n)��߀������İl(f��)չ��(qu��n)���l(f��)չ����KĿ��߀��Ҫʹ���w�е�ÿһ��(g��)�˶�������ܵ��l(f��)չ�ijɹ�����֮����(g��)�˰l(f��)չ��(qu��n)�oՓ�nj��ڂ�(g��)�w���˵İl(f��)չ��߀�nj�������(g��)��İl(f��)չ����������Ҫ�ăr(ji��)ֵ�����x��
����(��)(li��n)�χ��ļ�����(g��)�˷��ɵ�λ�Ĵ_�J(r��n)
����(li��n)�χ�1986�꡶�l(f��)չ��(qu��n)�����ԡ���1�l��ָ��:“�l(f��)չ��(qu��n)����һ�(xi��ng)���Ʉ��Z���˙�(qu��n)�������@�N��(qu��n)����ÿ��(g��)�˺����и���������Й�(qu��n)���c�����M(j��n)�����ܽ�(j��ng)��(j��)�����(hu��)���Ļ������ΰl(f��)չ�����@�N�l(f��)չ�У������˙�(qu��n)�ͻ������ɶ��ܫ@�ó��(sh��)�F(xi��n)��”[12]��2�lָ��:“���ǰl(f��)չ�M(j��n)�̵����w����ˣ��l(f��)չ���ߑ�(y��ng)ʹ�˳ɞ�l(f��)չ����Ҫ���c�ߺ������ߡ�”[12]��(g��)�ˑ�(y��ng)��(d��ng)�ǰl(f��)չ��(qu��n)�����w���@�N��ͬ�Ļ����J(r��n)֪�ٳ���(li��n)�χ��_�l(f��)Ӌ(j��)�����������o(j��)90���������“��l(f��)չ”���ᷨ����1990���ԁ���(li��n)�χ�ÿ��l(f��)���ġ���l(f��)չ��(b��o)�桷���Zؐ����(j��ng)��(j��)�W(xu��)��(ji��ng)��������?sh��)ف?middot;ɭ�O(sh��)Ӌ(j��)���u(p��ng)�r(ji��)�����l(f��)չ?f��n)�B(t��i)�ĸ��N��Ρ��䌍(sh��)���˙�(qu��n)�ę�(qu��n)�����w�ϣ�������(g��)�ˡ�Ⱥ�w�����(hu��)�����塢���ҵȵȡ�
����������(g��)������l(f��)չ��(qu��n)���w��Ӱ�����
������(g��)���ǂ�(g��)�˰l(f��)չ��(qu��n)�ę�(qu��n)�����w�������(qu��n)�����w�Ă�(g��)�ˣ���(hu��)�ܵ���Щ���ص�Ӱ푣��@Щ�����c��(g��)�˰l(f��)չ����(g��)�˰l(f��)չ��(qu��n)֮�g�������ӵ�(li��n)ϵ����Ҫ�J(r��n)��ؼ���̽����
����(һ)�A���c��(g��)�˰l(f��)չ��(qu��n)
�����ڬF(xi��n)��(sh��)���(hu��)�У��˂���(hu��)��?y��n)鲻ͬ�Ľ?j��ng)��(j��)�����Ρ��Ļ���λ�ȶ������֞鲻ͬ�ČӴΣ������(hu��)�W(xu��)�ϣ��Q֮���A�ӡ������(hu��)�У�ÿ��(g��)�˶����Ա��w�ڲ�ͬ���A�ӡ���ͬ���A����ζ����ͬ�Ľ�(j��ng)��(j��)�����Ρ��Ļ���r��������ÿ��(g��)�˵Ă�(g��)�˰l(f��)չ��������Ҫ��Ӱ푡�
�������ȣ��A�ӷ�ӳ�˂�(g��)�˵������r��Ӱ푂�(g��)�˰l(f��)չ��(qu��n)��(sh��)�F(xi��n)�ij̶ȡ���(g��)�˰l(f��)չ��(qu��n)�ڳ����cһ������x����ƽ�ȵģ����ڌ�(sh��)�H�����Єt�Dz�ƽ�ȵġ���?y��n)鲻ͬ�Ľ?j��ng)��(j��)��λ�����ε�λ���Ļ���λ�͛Q���ˌ�(sh��)�H�l(f��)չ?f��n)�r�c��(qu��n)�����Р�r�IJ�ƽ���ԡ���ͬ���A�ӱ�������ζ�������(hu��)�����е�ijЩ�������ƽ�ȡ�һ���f����̎�����(hu��)�^���A�ӵ��������ڽ�(j��ng)��(j��)�����Ρ��Ļ���̎�ڃ�(y��u)�ݵĵ�λ�����и��õ�����h(hu��n)����Ҳ�����@���^���ֵİl(f��)չ���܉��^�õ����аl(f��)չ�ę�(qu��n)����̎�����(hu��)�^���A�ӵ��ˣ��t������?y��n)���N����ʹ�䂀(g��)�˙�(qu��n)����ʹ���͂�(g��)�˰l(f��)չ���ޡ�
������Σ��A��Ӱ푂�(g��)�˵����(hu��)������Ӱ푂�(g��)�˰l(f��)չ��(qu��n)�����Р�r����(j��)���P(gu��n)�{(di��o)��������˂������(hu��)����Ȧ�������Ǹ�����̎���A�����P(gu��n)����ͬ�A�ӵ��˓��в�ͬ�����(hu��)�YԴ���^���A�ӵ��������ṩ���õĻ����l������(g��)��Ҳ���ܕ�(hu��)���@�N��(y��u)Խ�l�����@�ø��õİl(f��)չ�C(j��)��(hu��)����(qu��n)��Ҳ���܉���õ����С������^���A�ӵĂ�(g��)�ˣ�Ҳ�������y�ԫ@���^���A���ǘӵİl(f��)չ�C(j��)������(g��)�˰l(f��)չ��(qu��n)������Ҳ��(hu��)�S֮���ܵ����ޡ�
�����ٴΣ��A��Ӱ푂�(g��)�˵ăr(ji��)ֵ��(sh��)�F(xi��n)��Ӱ���l(f��)չ��(qu��n)�Č�(sh��)�F(xi��n)�̶ȡ������еČW(xu��)����ָ�����ĺ��^����������A��֮�g���P(gu��n)ϵ�Ǵ�������ƽ�Ⱥ����ġ��˲���Ó�x����̎�����(hu��)�h(hu��n)��������Ó�x����̎���A�Ӷ������ذl(f��)չ���A�Ӻ��A��֮�g���ڂ�(g��)�˵İl(f��)չ�YԴ�ϡ��l(f��)չ�C(j��)��(hu��)�ϵIJ�eҲ�ǿ��^���ڵġ���(d��ng)ǰ���S����I(y��)�ҡ������ˆT�����I(y��)���g(sh��)�ˆT��Ⱥ�w�İl(f��)չ���ӳ���ͪ�(d��)�������������(hu��)����������Ҫ�����ã��������İl(f��)չҲ������ߵ�Ҫ���������䌍(sh��)�F(xi��n)�����ăr(ji��)ֵ��
��������A��Ӱ푂�(g��)�˵ę�(qu��n)�����R(sh��)��Ӱ푂�(g��)�˰l(f��)չ�ę�(qu��n)���V���I(y��)�����Լ����������IJ�ͬ���Q�����˂��挦��(qu��n)���r(sh��)�đB(t��i)���Լ����R(sh��)�IJ�ͬ���ڬF(xi��n)�A�Σ��r(n��ng)��Ⱥ�w�������(hu��)��һ��(g��)�������ݵ�Ⱥ�w�������ڰl(f��)չ��(qu��n)���ܵ��ֺ��r(sh��)���ߏ�(qi��ng)�ҵę�(qu��n)�����R(sh��)���y�ԫ@���^�õę�(qu��n)���ȝ�(j��)����(d��ng)���(qu��n)���ܵ��ֺ��r(sh��)�����������Ǜ]�����R(sh��)���������x���[�̣������x������`���ķ�ʽȥ�S��(qu��n)���������x���`���ķ�ʽ�S��(qu��n)�����H�o���ڙ�(qu��n)���Č�(sh��)�F(xi��n)������?x��)����K���������Լ��İl(f��)չ�C(j��)��(hu��)��
����(��)�Ԅe�c��(g��)�˰l(f��)չ��(qu��n)
�����Ԅe�������W(xu��)���������W(xu��)��ʩ̫����������W(xu��)�ĸ�����С������W(xu��)��һ����1974�꣬��������W(xu��)�������Ⱥͽܿ��ֳ���ġ��Ԅe�����W(xu��)��������(bi��o)־���Ԅe�����W(xu��)���Q����ԓ�W(xu��)�f���Q���Ѓɂ�(g��)ǰ��l��:һ�����(hu��)�����γ�����Ůƽ�ȵ��^���Ů֮�g�܉�����أ��˴���ه;���dz��J(r��n)��Ů�������ϴ_��(sh��)���ڲ��������Փ����ָ���ģ�“�Ԅe��ɫ�������(hu��)��ɫ��һ�N����ָ�����˂����Ԅe��ͬ���a(ch��n)���ķ���һ�����(hu��)������Ʒ�|(zh��)������������Ů�������ֵIJ�ͬ�B(t��i)�ȡ��˸����������(hu��)�О�ģʽ��”[17]
�������ȣ������(hu��)�����ρ��f��Ҫ���^�挦��Ů���Ԅe���c(di��n)����ɵİl(f��)չ���������Ů�ڰl(f��)չ�еĿ��^Ҏ(gu��)�ɣ���ְl(f��)�]��Ů�Ԅe֮�L̎���M(j��n)�䂀(g��)�l(f��)չ��ʹ��������(hu��)�İl(f��)չ�����S����ʡ���Σ������Ԅe��ҕ�����،��Ԅe�IJ�^�ژ�(bi��o)�����̻���Ŀǰ�������(hu��)�͘I(y��)�ֲ��У��Ԅe���x߀���^��(y��n)�ء����磬����(j��)�������˿��ղ��ṩ�Ĕ�(sh��)��(j��)�Y�ϣ��҂������˽���Ů���Ԅe��ھ͘I(y��)��r���I(y��)��(g��u)���ϴ��ڵIJ�e��“���҇�Ů���I(y��)��(g��u)���У����ҙC(j��)�P(gu��n)���hȺ�M������I(y��)���I(y��)��λؓ(f��)؟(z��)��ռ1.0%�����I(y��)���g(sh��)�ˆTռ7.8%���k���ˆT�����P(gu��n)�ˆTռ3.2%���������������I(y��)�ďĘI(y��)�ˆT�Q��‘���I(l��ng)’����ô‘���I(l��ng)’Ů�ԃHռŮ�ԏĘI(y��)�ˆT��2.0%��”[18]
������������I(y��)�l(f��)չ�^���е��Ԅe���x���б�Ҫ����һЩ�ڂ��y(t��ng)�^���ό��Ԅe�̻����I(y��)��λ�����磬���y(t��ng)�^�����׃��@�̎��Ľ�ɫ�Ͷ�λ��Ů���ϣ������׃��Ľ����H�H��Ů�ԁ�������h(yu��n)�h(yu��n)����ģ��S�����(hu��)�İl(f��)չ���^����M(j��n)�������(hu��)Խ��Խ�����׃��Ľ�����(y��ng)���M(j��n)�н̎����@�����׃��˸�l(f��)չ�����ƴ������档�ٱ��磬�ڇ��ҙC(j��)�P(gu��n)���hȺ�M������I(y��)���I(y��)��λؓ(f��)؟(z��)�˵č�λ�ϣ�Ů���I(l��ng)��(d��o)�˵ı����Ǻܵ͵ġ�
����(��)�����c��(g��)�˰l(f��)չ��(qu��n)
��������������M(j��n)�з���������Ա��֞����������������������������ָ�����˂��M(j��n)�и��N���(d��ng)����횾߂���ձ��Ե������������˵��^������ӛ�����������������[19]����������ָ�����˂�����ijЩ���I(y��)�Ի��(d��ng)������߂��������������J(r��n)���nj��I(y��)�������电(sh��)�W(xu��)�����������v���L�������ȡ��@Щ�������������ձ��ԣ������˂��������A�x�Ļ��A(ch��)�ϣ�ͨ�^���ܽ��������(hu��)��(sh��)�`�Ȼ��(d��ng)���γɺͰl(f��)չ�����ġ�
����(һ)�˵��w���c�˵İl(f��)չ
�����w����Ҫָ�����˵����w���|(zh��)����“�M(j��n)���\(y��n)��(d��ng)��ڄ�(d��ng)����Ҫ�����w�������ȿ������\(y��n)��(d��ng)������Ҳ�������ڄ�(d��ng)������������ʽ�����w���(d��ng)����”[22]���w����Ҫ�������w�İl(f��)��ˮƽ�����˵��w���w�͡��I�B(y��ng)��������r�ȡ�����ָ�������J(r��n)֪���������^���ﲢ�\(y��n)������˼�S��Q���}���������˵��w�ܺ��������^���Ǵ��ڲ�ģ��@ȡ�Q��ÿ��(g��)�˵��z�������Լ�����A�x�IJ�ͬ���M���S��������ܽ����Լ�����(y��ng)Ӗ(x��n)�����˵��w�ܺ�������(hu��)����l(f��)չ׃����������Щ��������s���y�Ը�׃�ġ�������?y��n)��˵��w�ܺ������в���Ķ��˵İl(f��)չ��·���x���Լ��l(f��)չǰ�����Ǵ��ڲ�ͬ�ġ�
�����˵��w�܌��˵İl(f��)չ��Ӱ푡������Ǻ����w�ܵ�һ��(g��)��Ҫ��(bi��o)��(zh��n)������������J(r��n)�R(sh��)���S�����(hu��)�l(f��)չ�Լ��ƌW(xu��)���g(sh��)���M(j��n)��������ġ�Ŀǰ����Ľ������}�ѳɞ��t(y��)�W(xu��)����W(xu��)�����(hu��)�W(xu��)������W(xu��)�ȸ��W(xu��)���I(l��ng)��Ҫ̽ӑ�Ć��}�������f�������Ǵ��M(j��n)�˵�ȫ��l(f��)չ�ı�ȻҪ�����˵��w�ܠ�r���HӰ��w���ڄ�(d��ng)�ߵİl(f��)չ��߀Ӱ��X���ڄ�(d��ng)�ߵİl(f��)չ���oՓ�nj����w���ڄ�(d��ng)��߀���X���ڄ�(d��ng)�߁��f���������������c�l(f��)չ��ǰ���c���A(ch��)��
�����w���ڄ�(d��ng)����Ҫ���������w���M(j��n)�����a(ch��n)�ڄ�(d��ng)���ˣ��w���ڄ�(d��ng)�����c(di��n)��Ҫ���Լ�������Ļ��(d��ng)�������������Ĵ���ꐴ��x�죬���(y��n)���w�������������罨���I(y��)���r(n��ng)�I(y��)���}��(ch��)�bж�I(y��)���ɾ�I(y��)����Сú�G��ˮ��Ȯa(ch��n)�I(y��)�������w���ڄ�(d��ng)��IJ��T�����@Щ�I(y��)�ڄ�(d��ng)�У��w���ڄ�(d��ng)�ߵ��w�ܠ�B(t��i)ֱ��Ӱ푵����Ĺ���Ч��������ˮƽ���l(f��)չǰ�������磬���ڏ��°��\(y��n)�������ˁ��f���w���Ǻ�����������ȵģ��w��Խ�ã���������Խ�࣬��(d��ng)Ȼ����Խ�ߡ�
���������w���ڄ�(d��ng)�����������ڣ��ڄ�(d��ng)����Ҫ��Ϣ�ͻ֏�(f��)�����ٴήa(ch��n)���ڄ�(d��ng)����ͬ�r(sh��)��?y��n)錦���w�������Ĵ���Щ�w���ڄ�(d��ng)�L�ھ��������w��ijһ��λ��M�����L���������a(ch��n)���ړp��߀��Щ�����h(hu��n)���T��ߜء��ۉm�����ȣ��@Щ����(hu��)�����w�Ľ����a(ch��n)����ͬ�̶ȵēp���������w���ڄ�(d��ng)�߁��f�����䑪(y��ng)��(d��ng)��ҕ�����w�ܽ�������?y��n)齡�����w�ܿ���������Ҫ�ġ�����Ψһ�������c�l(f��)չ��;������ˣ��w���ڄ�(d��ng)�ߑ�(y��ng)��(d��ng)�ƌW(xu��)���Ź�������Ϣ�������w�z���m�ȵ��M(j��n)���\(y��n)��(d��ng)������ͬ�r(sh��)���Һ����(hu��)��(y��ng)�ӏ�(qi��ng)�c���ƌ��w���ڄ�(d��ng)�ߵ����(hu��)�����ƶȡ�
����(��)�˵������c�˵İl(f��)չ
�����˵����ܣ���ָ�������е��ǻ���������һ���ˁ��f���@�����f�˵����ܣ���ָʹ���܉����Ђ�(g��)�˰l(f��)չ��(qu��n)����һ�����ܣ���һ�������ձ���е��Z�ԡ�߉�����g��֫�w�\(y��n)�������H�����������J(r��n)֪�ȷ����������һ��(g��)�������������(hu��)����(d��ng)ȻҲ������ķ������(hu��)����(y��ng)ԓʹÿ��(g��)�˻����Լ������ܶ������ձ�İl(f��)չ��(qu��n)����
�����;����������ܵ��ˁ��f������������Ҳ����ʹ���܉����Ђ�(g��)�˰l(f��)չ��(qu��n)������Щ�������˵��������ܣ��������Z�ԡ�߉�����g��֫�w�\(y��n)���������ȷ��檚(d��)�ص����x�������L��һ��(g��)���õ��������(hu��)������Ҫʹ��Щ�����������ܵ����܉�����Լ����������ܶ��õ��Ϸ��ġ���ֵĂ�(g��)�l(f��)չ��
�������X���ڄ�(d��ng)�߁��f�������Ǿ����������ܵ��I(y��)Ⱥ�w�������������f�����ܸ����Ъ�(d��)�ص����x���X���ڄ�(d��ng)�����c(di��n)��Ҫ����ه�X��ȥ������˼���c�Д࣬������Փ�����ߡ��ƌW(xu��)�ҡ�ˇ�g(sh��)�ҡ����ҡ��Ɏ��ȡ�
���������˵��И���(j��ng)ϵ�y(t��ng)�����ܿ��Ը���(j��)�^���Ľ�(j��ng)�(y��n)�Լ���δ�������Ե��A(y��)�y�Ķ������c��Q��(d��ng)�µĆ��}�����˵������M���У����ܵăr(ji��)ֵ�������Ҫ�ġ������(hu��)�О����x�ĽǶȳ��l(f��)�����]���ܣ�������(sh��)�����x�W(xu��)�����J(r��n)��:“�\(y��n)�����ܵ��^�̾������t���M�����x���ض��h(hu��n)���̼��ķ���(y��ng)���^�̡�”[23]
���������X���ڄ�(d��ng)�߁��f���˵İl(f��)չ�mȻȡ�Q�ںܶ�����أ����������ںܴ�̶��ό��˵İl(f��)չ�����P(gu��n)�I���á������ЌW(xu��)�����f������vʷ�l(f��)չ����“һ��(g��)�ܳ��ƌW(xu��)�����������(hu��)ؕ�I(xi��n)�^���ǿ����ε��˔�(sh��)���ӡ��w������(qi��ng)�Լ���������Ο������ܽ�Q�ġ�”[24]140���������w���ڄ�(d��ng)���X���ڄ�(d��ng)�İl(f��)չ�~�M(j��n)������(g��)���(hu��)��(y��ng)�γ�����֪�R(sh��)�������˲ŵķՇ���������ߺ��_�l(f��)�˂�����������(d��ng)ǰ���H�������P(gu��n)�I������֪�R(sh��)���˲ŵĸ�����“�l������֪�R(sh��)���˲ţ�����ְl(f��)�]�����ã��l�������@��������ռ��(y��u)�ݡ�”[24]141
���������ڂ�(g��)�˰l(f��)չ��(qu��n)�ϵ���ҪĿ��(bi��o)������Ҫʹÿ��(g��)�˰������в�ͬ���ܠ�B(t��i)���˸����������@�ó�ֵİl(f��)չ��ͬ�r(sh��)����������Ҫʹ��Щ�������ϳ��F(xi��n)�ϵK���˫@���e���o(h��)����ʹ���܉�@��������õİl(f��)չ�l���c���g�����˙�(qu��n)��ƽ�Ⱥͱ��o(h��)����Ŭ�������������������ˮƽ��
����(��)���Ɍ��ښ����˵ı��o(h��)
���������l(w��i)���M�����ښ����Ķ��x��:“����ȱ�ݶ�ȱ��������������������ʽ����ij�N�������(d��ng)��������”�҇��������˱��Ϸ�����2�lҎ(gu��)��:“��������ָ�����������������w�Y(ji��)��(g��u)�ϣ�ij�N�M�������܆�ʧ���߲�������ȫ�����߲��ֆ�ʧ��������ʽ����ij�N���(d��ng)�������ˡ�”[25]�oՓ�������l(w��i)���M�����ښ����Ķ��x��߀���҇��������˱��Ϸ������ښ�����Ҏ(gu��)�������J(r��n)�隈���˰����w���ϻ������ϴ���ȱ�ݵ��ˣ�������?y��n)��w���ϻ������ϴ���ȱ�ݣ����������������һ���������c���(hu��)��“̎��ij�N������λ���������ƻ���Kԓ�˰l(f��)�]�������g���Ԅe�����(hu��)�c�Ļ������ؑ�(y��ng)�ܰl(f��)�]���������á�”
�����ښ����˵İl(f��)չ?f��n)�rָ��(bi��o)�У��͘I(y��)�ǚ�������������|(zh��)������(sh��)�F(xi��n)�����l(f��)չ����Ҫƽ�_(t��i)����Ҫ������ͨ�^�͘I(y��)�����������ȿ��ԫ@�÷�(w��n)�������룬ʹ�����������܉�������������ȫ��ه���(hu��)�c��ͥ�Ĺ��B(y��ng);��Σ����ԅ��c���(hu��)��ʹ�����İl(f��)չ�������(hu��)�İl(f��)չ֮�С�
�����b�ښ������ڰl(f��)չ�ϵ������ԣ��Լ��������ڌ�(sh��)�F(xi��n)�����l(f��)չ�����R�����y�c�ϵK�����Һ����(hu��)��(y��ng)��(d��ng)�Ӵ����˰l(f��)չ��(qu��n)���ı��ϡ�������(g��)���(hu��)������f�����(hu��)��(y��ng)�e�O�D(zhu��n)׃�^����܃H�H��“�t(y��)�����}”��“�������}”[28]�ĽǶȳ��l(f��)�팍(sh��)�F(xi��n)�������˙�(qu��n)���ı��ϣ�����(y��ng)ԓվ�ڂ�(g��)�˰l(f��)չ��(qu��n)�ĸ߶ȁ����������˵������c�l(f��)չ���}���e��Ҫ������ҕ�^�
�������ɑ�(y��ng)��(d��ng)�ӏ�(qi��ng)�������˰l(f��)չ��(qu��n)���ı��ϡ��ć��H������f��2006��(li��n)�χ����(hu��)ͨ�^�ˡ������˙�(qu��n)�����H���s�����@��(li��n)�χ��vʷ�ϵ�һ��(g��)ȫ�汣�o(h��)�����˙�(qu��n)���Ĺ��s����ǰ�����P(gu��n)�ښ����˵������Є�(d��ng)�V�I(l��ng)���͡������˙C(j��)��(hu��)���Ș�(bi��o)��(zh��n)Ҏ(gu��)�t���ȇ��H�˙�(qu��n)�ļ����C���mȻ���߂䏊(qi��ng)�Ƶļs���������nj��ں�P(y��ng)�����c���o(h��)�����˙�(qu��n)���ľ��������Ҫ�ăr(ji��)ֵ�����x���@�ɂ�(g��)���H�ļ��c�������˙�(qu��n)�����H���s���������Ƅ�(d��ng)���皈�����I(y��)�İl(f��)չ��
�����ć���(n��i)������f���҇��ǡ������˙�(qu��n)�����s��������l(f��)����֮һ�����ں����ˡ������˙�(qu��n)�����H���s��֮����(j��)���s�ľ�����(n��i)���P(gu��n)�ķ��ɷ�Ҏ(gu��)�M(j��n)������ӆ���ѳ����γ����ԡ�����������A(ch��)���ԡ������˱��Ϸ�����������Ě����˙�(qu��n)�����ϵķ��ɷ�Ҏ(gu��)�wϵ�����ښ����˵������l(f��)չ���ԣ�ƽ�ȵؽ��ܽ����cƽ�ȵ��c�͘I(y��)�ǚ����˵ĺ�������ֻ��ͨ�^���ܽ��������c�͘I(y��)�����ܝM�㚈���˵�����������������|(zh��)�������c���(hu��)���ʹ�����õ��l(f��)չ���������İl(f��)չ�������(hu��)�İl(f��)չ֮�С�������?y��n)�����c�͘I(y��)���ښ����ˌ�(sh��)�F(xi��n)�����l(f��)չ��(qu��n)����Ҫ���ã����Һ�������(y��ng)��(d��ng)�������˄ڄ�(d��ng)�͘I(y��)�y(t��ng)�IҎ(gu��)�������䄓(chu��ng)��ڄ�(d��ng)�͘I(y��)�l����ͬ�r(sh��)�ڷ��Ɍ��棬��(y��ng)��(d��ng)��ֱ��Ϛ����˵��ܽ�����(qu��n)�̈́ڄ�(d��ng)�͘I(y��)��(qu��n)�Č�(sh��)�F(xi��n)��
�������ˣ��҇����������͡������˱��Ϸ������ښ����˵ę�(qu��n)������ԭ�t�ԵĿ��wҎ(gu��)����ͬ�r(sh��)����������Ҏ(gu��)���棬�������˾͘I(y��)�l�����c�������˽����l�������T�͚����˾͘I(y��)��(qu��n)�c�ܽ�����(qu��n)���˾��w��Ҏ(gu��)�����@�ɂ�(g��)�l�����C��ּ����ߚ����İl(f��)չ�����������Ƅ�(d��ng)�����˰l(f��)չ��(qu��n)�Č�(sh��)�F(xi��n)������Ҫ�����x�����磬�������˾͘I(y��)�l����Ҏ(gu��)��:“�����ˑ�(y��ng)��(d��ng)����������|(zh��)������(qi��ng)�͘I(y��)������”
����������(g��)������l(f��)չ��(qu��n)���w���x��(w��)���X
������(g��)�˰l(f��)չ��(qu��n)�Č�(sh��)�F(xi��n)��r�Q���ڶ�N���أ��������邀(g��)�˰l(f��)չ��(qu��n)����Ҫ�x��(w��)���w�����Ԟ邀(g��)�˵İl(f��)չ�ṩ��(j��ng)��(j��)�����Ρ��Ļ������(hu��)���ϵȸ��(xi��ng)�ƶȣ��邀(g��)�˰l(f��)չ��(qu��n)�Č�(sh��)�F(xi��n)��(chu��ng)���ƶȭh(hu��n)�����ṩ��(qi��ng)�Ʊ��ϡ����ھ��w�ķ����P(gu��n)ϵ�У���(g��)�˰l(f��)չ��(qu��n)���x��(w��)���w�����Ǿ��w�Ă�(g��)�ˣ���(hu��)�䌍(sh��)���S����(g��)�w���ϡ���(g��)�˲��H�nj�(sh��)�F(xi��n)�l(f��)չ��(qu��n)�ę�(qu��n)�����w��ͬ�r(sh��)Ҳ�nj�(sh��)�F(xi��n)�l(f��)չ��(qu��n)���x��(w��)���w���@��Ҫ������(y��ng)��(g��)�w���б�Ҫ���x��(w��)���X�����m��(y��ng)���w���ݵ���Ҫ��
����(һ)�����x��(w��)���w�Ă�(g��)��
���������˙�(qu��n)���x��(w��)���w�����邀(g��)�˰l(f��)չ��(qu��n)���x��(w��)���w�����Ƕ�Ԫ�ġ��������LJ��һ�����������������ij��(g��)�ض��Ă�(g��)�ˡ���(g��)�˼������(qu��n)�����w��Ҳ�����x��(w��)���w�����邀(g��)�w�����ڂ�(g��)�˰l(f��)չ��(qu��n)���ķ����P(gu��n)ϵ֮�У����������Й�(qu��n)��Ҳ�Г�(d��n)�x��(w��)�����x��(w��)���w��ҕ�ǁ����죬���������J(r��n)�邀(g��)������������ձ���x��(w��)���w�����������P(gu��n)�ĸ��N�����P(gu��n)ϵ֮�С��ڇ��H���(hu��)�����еķ����ļ��o���϶���(g��)�����邀(g��)�˰l(f��)չ��(qu��n)�x��(w��)���w�ĵ�λ������������˷N�N�����ϵ�Ҫ��
����(��)�J(r��n)�R(sh��)���������˙�(qu��n)��
���������x��(w��)���w������J(r��n)�R(sh��)����������(y��ng)���w�ڂ�(g��)�˰l(f��)չ����ę�(qu��n)�����J(r��n)�R(sh��)��(qu��n)�������ؙ�(qu��n)�����Ǚ�(qu��n)�����Դ��ں͌�(sh��)�F(xi��n)��˼����A(ch��)���R��˼�J(r��n)�飬�˵ı��|(zh��)��һ�N���(hu��)���ڣ���“���N���(hu��)�P(gu��n)ϵ�Ŀ���”���˲�����Ó�x���(hu��)����(d��)�������c�l(f��)չ����(qu��n)���Č�(sh��)�F(xi��n)�����Ó�x�c��(qu��n)�����w���P(gu��n)�����(hu��)�P(gu��n)ϵ����(d��)�Ԍ�(sh��)�F(xi��n)��
�������W(xu��)�ҵ��K�J(r��n)�飬�˲����ܰ����Լ��]�еĺ����M(j��n)�����(hu��)��ǰ�������еę�(qu��n)�����M(j��n)���(hu��)�Ё�����֮����ֻ�����M(j��n)�����(hu��)֮����ܓ��Й�(qu��n)������?y��n)����M(j��n)�����(hu��)�ͱ�ȻҪ���������˰l(f��)���@���ǘӵ��P(gu��n)ϵ[28]��һ��(g��)�˵ę�(qu��n)���J(r��n)�R(sh��)���ȑ�(y��ng)ԓ�����������(qu��n)�����J(r��n)�R(sh��)��Ҳ�������e�˙�(qu��n)�����J(r��n)�R(sh��)������fÿ��(g��)��ֻ�P(gu��n)�ĺ��P(gu��n)ע�Լ��ę�(qu��n)������ô������ζ������(hu��)�������˵ę�(qu��n)�����������˙�(qu��n)�������أ����ǵ����}�����Ƿ��Ɇ��}���oՓ�Ǐĵ��µ�ҕ�dz��l(f��)��߀�Ǐķ��ɵ�ҕ�dz��l(f��)���҂�����횏�(qi��ng)�{(di��o)�������˙�(qu��n)�������ء�
����(��)�J(r��n)�R(sh��)�����������x��(w��)
������ǰ�������x��(w��)���w���ؙ�(qu��n)���Ǚ�(qu��n)�����Դ��ں͌�(sh��)�F(xi��n)�Ļ��A(ch��)���x��(w��)���w���x��(w��)���J(r��n)֪�c����������(y��ng)��(qu��n)�����Ԍ�(sh��)�F(xi��n)����Ҫǰ�ᡣ�ھ��w�ę�(qu��n)���x��(w��)�P(gu��n)ϵ�У�ÿһ��(g��)�˶���(y��ng)��(d��ng)����(qi��ng)�����Լ��x��(w��)���J(r��n)֪����(qu��n)���c�x��(w��)���������ģ��]���˿���ֻ���ܙ�(qu��n)�������������x��(w��)��ÿһ��(g��)�˰l(f��)չ��(qu��n)���Č�(sh��)�F(xi��n)������ه�����P(gu��n)�x��(w��)���w�������c�����顣��(d��ng)�x��(w��)���w���X���з������x��(w��)�r(sh��)����(qu��n)���˵İl(f��)չ��(qu��n)��(sh��)�F(xi��n)�t�^�����������(d��ng)�x��(w��)���w�����������ֺ���(qu��n)���˵İl(f��)չ��(qu��n)���r(sh��)����(qu��n)���˵İl(f��)չ��(qu��n)��(sh��)�F(xi��n)�t��(hu��)�ܵ��ϵK���x��(w��)�������Ǚ�(qu��n)����(sh��)�F(xi��n)����Ҫ���ϡ���(qu��n)���ļ���ę�(qu��n)�������䌍(sh��)���F(xi��n)��(sh��)�ę�(qu��n)������������һ��(g��)���(hu��)�ط�������B(y��ng)�ɡ��ط������ںܴ�̶�����ه���w�F(xi��n)�����(hu��)��ÿһ��(g��)�ˌ����x��(w��)���J(r��n)֪�����С��ط������е������Ҫ��Ҳ�з��Ɍ����Ҫ���Ɍ����Ҫ�����������Ҫ����ÿһ��(g��)���w�ę�(qu��n)���x��(w��)�P(gu��n)ϵ��(d��ng)�У��������x�ϵ��ط�����Ҫ��ÿһ��(g��)�˶���(y��ng)��(d��ng)���X�������P(gu��n)�ķ����x��(w��)���Ķ��������˵ę�(qu��n)�����������ʹ��
���������x��(w��)���J(r��n)֪�����H�H�nj��x��(w��)���w��Ҫ��(qu��n)�����w����ʹ�����(qu��n)����ͬ�r(sh��)��ͬ�ӑ�(y��ng)��(d��ng)����(qi��ng)�������x��(w��)���J(r��n)֪���҇������������_Ҏ(gu��)��:“�κι������Б����ͷ���Ҏ(gu��)���ę�(qu��n)����ͬ�r(sh��)������Б����ͷ���Ҏ(gu��)�����x��(w��)��”һ���ְl(f��)չ��(qu��n)�������ͼ��Ǚ�(qu��n)�������x��(w��)�����磬�҇�����Ҏ(gu��)�������Єڄ�(d��ng)�ę�(qu��n)�����x��(w��)���������ܽ����ę�(qu��n)�����x��(w��)���ڄ�(d��ng)��(qu��n)���ܽ�����(qu��n)���邀(g��)�˵ă��(xi��ng)��Ҫ�İl(f��)չ��(qu��n)������������ʹ�ڄ�(d��ng)�ͽ��ܽ�����(qu��n)����ͬ�r(sh��)��������Єڄ�(d��ng)�ͽ��ܽ������x��(w��)��ͬ�r(sh��)��߀����M(j��n)һ���J(r��n)�R(sh��)����(qu��n)�����w����ʹ�����l(f��)չ��(qu��n)����ͬ�r(sh��)�����ó�������Ҏ(gu��)�����ȣ����÷��K�e�˰l(f��)չ��(qu��n)���Č�(sh��)�F(xi��n)���˕r(sh��)��(qu��n)���˄t�ę�(qu��n)�����w�D(zhu��n)�����x��(w��)���w�����磬�˂�����ʹ�Ļ��ʘ���(qu��n)����ͬ�r(sh��)�������ֺ����˵���Ϣ��(qu��n)����(qu��n)������ʹһ����������Ҏ(gu��)�����ȣ��ֺ����������棬��(qu��n)���˾͑�(y��ng)��(d��ng)�Г�(d��n)����؟(z��)�Ρ�
�����x��(w��)���w��������л��߲��m��(d��ng)�����x��(w��)���Ϳ��ܱ��ظ�����l(f��)�V�A�ȡ�һ���x��(w��)�˱����P(gu��n)���əC(j��)�P(gu��n)�_�J(r��n)��δ�����x��(w��)��δ�m��(d��ng)�����x��(w��)������(g��u)���`�s�����`�����Ϳ����ܵ����ɵď�(qi��ng)�ơ����əC(j��)��(g��u)�Ϳ��ܑ�(y��ng)��(qu��n)���˵�Ո������x��(w��)�˲�ȡ��(qi��ng)�ƴ�ʩ����ʹ�������x��(w��)���x��(w��)���w�����X�����c����(qi��ng)�����У����nj����x��(w��)�����У��������(n��i)����Ч����Ӱ푅s�ǘO����ͬ�ġ�
�����x��(w��)���w�IJ����л��߲��m��(d��ng)���У���(hu��)�o��(qu��n)����������_��ʹ��(qu��n)�����w�ę�(qu��n)���o����(sh��)�F(xi��n)��Ҳ��(hu��)�o���ҵĹ���(qu��n)���C(j��)��(g��u)����ؓ(f��)��(d��n)�����ڲ������x��(w��)�����w�����ˏ�(qi��ng)��������֮�⣬߀��(y��ng)�o�葪(y��ng)�е��Ʋã�ʹ֮������ȡ��Ӗ(x��n)�����X�����Լ����x��(w��)��Ҳʹ���(hu��)�������ɆT���������x��(w��)���w������ȡ��Ӗ(x��n)���Ķ�У���Լ����О飬�e�O���m��(d��ng)?sh��)������x��(w��)����(g��)�ˌ��ڰl(f��)չ��(qu��n)�x��(w��)���J(r��n)֪�c���У��،������������˰l(f��)չ��(qu��n)�ĸ��Ì�(sh��)�F(xi��n)���@�������P(gu��n)�x��(w��)��(y��ng)�еăr(ji��)ֵָ��
�������P(gu��n)Փ�ķ�����x�����W(xu��)��֮˼�����Z���Ι�(qu��n)��
����[ժ Ҫ] �������Pһ�N�Ą��Z���Ι�(qu��n)�����ڃ�(n��i)�ݺͽY(ji��)��(g��u)��������һ����ȱ�ݣ������l(f��)����Փ��͌�(sh��)��(w��)�猦����ڵăr(ji��)ֵ�Ժͺ����ԵĠ��h�����ľ̈́��Z���Ι�(qu��n)���ă�(n��i)�ݵ�����ͽY(ji��)��(g��u)������(g��u)���M(j��n)�М\�h����ʾ˼����
- ����e(cu��)λ��Փ�µij���С�f�̌W(xu��)�о�
- ���l(xi��ng)���Ї�����(d��o)�x�n�̌W(xu��)�O(sh��)Ӌ(j��)˼��
- ���Լ�����һ�N�����u(p��ng)���ɵġ��o�m܇�g��
- ����ý��ġ����^Ԋ���x�켽���ո���(j��)���ČW(xu��)��������Є�(d��ng)�T
- �vʷʹ�����Ļ������c���w��(j��ng)�(y��n)�����Ƶ¡����v��Ⱥɽ��ӑՓ������
- ���顰�Ļ�������ý�顱���մ��Ļ�o(j��)�Ƭ�ăr(ji��)ֵ����
- �����Y�ϵķ��g�����������о�
- ���A(y��)�O(sh��)��Փ���x����ԡ֮��������Ĭ���Z
- �zӰˇ�g(sh��)�ڮa(ch��n)Ʒ�O(sh��)Ӌ(j��)�еđ�(y��ng)���c�о�
SCI�ڿ�Ŀ�
���T�����ڿ�Ŀ�
SCIՓ��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ڿ�Ͷ���֪
- 2025-04-03�؏�(f��)SCI�����˵IJ��Լ��؏�(f��)�ŵ�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t(y��)�W(xu��)4
SSCIՓ��
- 2025-02-28�������о����I(y��)Ӣ��Փ�Ŀ��x��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ڿ��օ^(q��)��Ӱ�
- 2025-02-10��(j��ng)�܌��I(y��)���ٰl(f��)��ssciՓ�ĵ�����
EIՓ��
- 2025-04-02Ҋ����z�����EI��(hu��)�h���]��ƥ��
- 2025-03-05EI��(hu��)�h���İl(f��)Փ�ģ����ָ��(d��o)
- 2025-03-01EI��(hu��)�hՓ��ֵ�ðl(f��)��?2025EI��(hu��)�h
SCOPUS
- 2025-02-07ʲô��ȫ���͔�(sh��)��(j��)��?scopus��(sh��)��(j��)
- 2025-01-24scopus�l(f��)�����¸�ʽ��ָ��
- 2024-11-19Scopus��䛵Ľ���������ڿ�
���g��ɫ
- 2024-11-22���H�����ڿ��l(f��)��Փ�đ�(y��ng)ԓ��ʲô
- 2024-11-22���H���Ľ̎����ڇ��H�����ڿ��l(f��)
- 2024-11-22���H�����ڿ��u(p��ng)�Q���J(r��n)��
�ڿ�֪�R(sh��)
- 2025-04-01��(f��)�ϲ��ϿƌW(xu��)�c����Փ��Ͷ��word
- 2025-04-01��ȫ����Փ�����]�m��Ͷ�IJ�ͬ��(j��)
- 2025-03-2915��������p�����ڿ�!�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