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的鄉里控制體系及其變化
時間:2020年06月19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西周時期,齊國遵循周制,以國、野二元體制作為基本統治制度,“參其國而伍其鄙”,即將“國人”區分為三部,而將其所統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劃為五個區。齊桓、管仲改革,重整國、鄙二元體制:在國中實行兵農合一制;在鄙中實行軍、民分治之制。無論國、鄙,其鄉里控制體系,皆由伍或軌(五家)、里或邑(三十家、五十家或百家)、鄉(二百五十家或五百家)三級組成。金文所見春秋晚期齊國的鄉里控制制度,當是邑(鄉)—里二級制。陶文所見戰國時期齊國的城鄉控制體系,在臨淄城中實行“閭—里”制,在鄉村地區則實行“卒—鄉—里”制,其控制結構與春秋時期大致相同,只是在“鄉”(邑)之上增加了“卒”(又分置左右敀)。委派“立事”分治臨淄城內外各區(“閭”),以及在“鄉”之上設立“卒”,說明齊君強化了對城鄉社會的直接控制,而貴族在城鄉社會中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則受到削弱。
關鍵詞:鄉里;齊國;控制體系;今本《管子》;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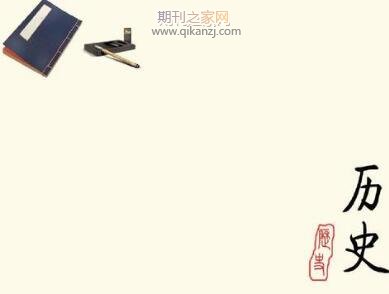
齊在立國之初,大抵遵循周制,以國、野二元體制作為基本統治制度①。《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封于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種,其強族有薄姑氏。周初銅器方鼎銘文曰:隹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尃古,咸َ2。“尃古”,即薄姑,或作蒲姑。《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0年)晏嬰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凌,殷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③則知齊國所統治的當地土著人群,乃是包括薄姑在內的諸種人群。小臣(或釋作“”)(簋)銘文曰:
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師征東夷。唯/十又一月,遣自師述/東,伐海眉。戉復/歸才牧師,白懋父承/王令易自率征師五/貝。小臣蔑歷貝,/用乍寶奠彝。④銘文記伯懋父率殷八師,征伐反叛的東方海眉地區。“海眉”,當即海湄,亦即濱海地域。“五”之“”從“鹵”,顯指濱海鹽鹵之地。五,蓋伯懋父將征服之地分為五個區域。此五,很可能就是西周時期齊國統治“野人”(夷人,包括薄姑等)的五個區域,或即后來《管子》所說圣王之治其民“叁其國而伍其鄙”中的“五鄙”。
歷史方向論文范例:本雅明歷史哲學維度中的“靈韻”概念*
《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治國,“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⑤,則齊對于統治區內的土著人群,以寬簡治之,遂得人民多歸之。“伍其鄙”既有其歷史淵源,“叁其國”亦有可能。換言之,齊國在建國之初,很可能即將國人區分為三部,而將其所統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劃為五個區。
受到資料限制,我們對西周時期齊國的鄉里制度方式所知甚少,然今本《管子》各篇以及齊地所出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陶文,卻給我們認識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鄉里控制體系及其變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本文即試圖細致分析今本《管子》各篇有關齊國治理的言論,以盡可能窺知春秋時期齊國鄉里制的某些真相;綜合使用今見齊地所出春秋晚期至戰國的陶文,考證其中所見與鄉里控制相關的一些職名、地名,以闡明其義,并將之聯系起來,以形成對戰國時期齊地鄉里制的總括性認識;最后則將今本《管子》等傳世文獻有關齊國鄉里制的記載,與陶文所反映的齊國鄉里制的某些實際情況,加以綜合、比較,以究明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鄉里制度的基本結構與實質。
一、今本《管子》所述齊國鄉里制及其變化
《管子·小匡》詳記齊桓公與管仲之問答,錄管仲所對之改革方略,云:管子對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
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率),[卒](率)有長。十[卒](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①“參其國而伍其鄙”,《國語·齊語》韋昭注:“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②。則“鄙”即《周禮》所說之“野”。因此,管子的設計,乃是遵循“昔者圣王之治”,將齊國的“國人”分為三部分:桓公親領一部,十一鄉;高子、國子兩個上卿各領一部,分別為五鄉,即所謂“參國”,即三分其國(當理解為把國人分為三部分,不能理解為在空間上把“國”分為三部分)。齊公與高子、國子各為一軍,是為三軍。
國人的編組,實行軌—里—連—鄉四級制,軌五家,里五十家,連二百家,鄉二千家。鄙人則分為五,故稱為五鄙,每鄙各置有屬,每屬三鄉,是為十五鄉。鄙人的編組,實行軌—邑—卒—鄉四級制。屬帥(或作師)掌管“武政”,鄉良人統管“文政”。五鄙之中文、武分途,似乎說明其屬帥非常設之職,僅在有武事時置帥以領軍。而其所領之軍,大抵亦與《周禮》“遂人”所領之輔助兵相似。《管子·小匡》說齊桓公接受了管子的計劃:
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搜,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于郊。
③據《國語·齊語》,此段敘述乃是指“國”中之制。軌—里—連—鄉的居民編組,與伍—小戎—卒—旅的軍事編組相對應。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既為平時居民編制各級組織的首長,也是戰時軍隊編制的各級指揮官。“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④,就是兵農合一制。每旅二千人,國君直接領十一鄉十一旅,為一軍,共有二萬二千人;國子、高子各領五鄉(五旅),各有萬人,各為一軍,合為四萬二千人。今本《管子·小匡》未述及管子規劃的制度在“鄙”中實行的情況。《國語·齊語》記管子回答桓公“定民之居若何”時說:
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焉;立五正,使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五家為軌,邑有六軌、三十家,卒三百家,鄉三千家,縣九千家,屬九萬家,齊有五屬,各置大夫領之,當有四十五萬家。《國語·齊語》又說:“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其寡功者而謫之。”“五屬大夫于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①那么,在鄙中的邑—卒—鄉—縣—屬體系似確曾建立起來。
管仲、齊桓在鄉里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分別國、鄙,國鄙異制方面,是遵循“周制”原則的②。較之于“周制”,最大的變化,是在編組國人的“里”之上增加了“連”(二百家)和“鄉”(二千家),在編組鄙人的“邑”之上增加了“卒”(三百家)和“鄉”(三千家)。《禮記·王制》“十國以為連”、“三十國以為卒”句下鄭玄注:屬、連、卒、州,“猶聚也”③。連、卒都有集合、聚集之義,與“族”相同。《管子·小匡》于記在國中實行軌—里—連—鄉之制后,接著記載說:“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國中二十一鄉之長皆向齊桓公報告,說明鄉是齊之“國”最重要的行政層級。
鄉長舉其鄉之賢者,“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又“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又說“士與其為善于鄉,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不如為善于家”④。其辭皆徑稱“鄉里”,而未及二百家之連,說明在軌、里、連、鄉四級中,里與鄉比較重要。同樣,在齊桓公對五屬大夫的考察中,鄉和邑也比較重要。《管子·小匡》《國語·齊語》所述春秋初期齊國的鄉里制,雖然略有差異,然大致相同。然而《管子·立政》篇所述,卻與《管子·小匡》《國語·齊語》所述有很大不同: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闬,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
……凡孝悌、忠信、賢良、俊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⑤這里的敘述,起首謂“分國以為五鄉”,然其下文又說:“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廟,致屬吏,皆受憲。”⑥則其所述“分國”之“國”,仍然是《管子·小匡》《國語·齊語》所說的“參其國而五其鄙”之“國”。按照這里的說法,齊將“國”分置五鄉,而將“鄙”分置五屬。五鄉之制與齊桓、管仲所定的二十一鄉之制大異,若其屬實,則此處所述,必當是齊國后來調整之后的制度。且五鄉與五屬均直接受憲于君,不再有“高子之鄉”“國子之鄉”,顯然君權得到了強化。根據這里的說法,是把“國”分為五個鄉,鄉各有五個州;每州有十個里,每里有十個游。據鄉、州、里之間的關系推論,每游當有五個什、十個伍,亦即五十家。若然,則里有五百家,州有五千家,而鄉有二萬五千家,那么,齊的“國”共分為五鄉,當有十二萬五千家。
這個制度,與齊桓、管仲改革時所定的國、鄙分治之制不合,與齊國軍制亦不相合。在這個制度設計中,里成為鄉村控制的基本單元與居民居住的基本單元,每個里都筑有“障”(土垣),堵塞旁出的小路(匿),出入道路受到管制(“一道路、專出入”)。里有司稱為“里尉”,應當是武職。里中居民出入、衣服、日常生活均受到伺察管制,其軍事化程度顯然得到了強化。《管子·立政》雖述及五屬大夫,然未及鄙中鄉里之具體建制。《管子·乘馬》篇云: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里](暴),五[里](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之)。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里](暴),五[里](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
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①里—部—聚—鄉—方,是田地分劃制度;伍—連—里—鄉—都,是居民編組制度;聚—離—制—田—夫—家,則是役制。事者,侍也。所謂器制,則當是出軍資制度,每乘有甲士、白徒若干。這里所述的制度,不能完全通解。其上文述及山林澤藪,而上引文字中述及事制(役事)與器制,卻不及軍制,并沒有軍隊編制與其相配套,說明它應當是適用于“鄙”中的制度。若這一認識不誤,那么,此處所述,可能就是與《立政》篇所述國中之制相配套的“鄙”中之制。這里的記述,每“里”有五十家,“鄉”有二百五十家,“都”有千家,那么,“都”再上一級的編制,應當就是“屬”。今本《管子·度地》篇的成文年代明顯較晚,其述管子之言曰:
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②“別制斷之”,謂分別其地,制之斷之。“州者謂之術”,蓋地數充滿得為州者,為之術,即滿州者,分為若干術;不滿州者謂之里,當解作不滿一州者,分劃為若干里,意為分術為里。
此段言辭淺顯,且霸國之謂,非齊桓管仲時代之所有,當是后世觀念。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雖言及“別制斷之”,即以不同制度治理不同的地域,然其下所述,卻是里—術—州—都—國的一整套統一制度,并無“別制”,更不再有國、鄙之別。每“里”有百家,每“術”千家,則“州”有萬家,“都”有十萬家。《管子·度地》篇又借管子之口,引述齊國法令說:
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洲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余、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板、筑各什六,士車什一,雨軬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后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后時。
①這段文字,頗多問題,其成文當甚晚,或晚至漢時。其第一、三兩段,當可相聯讀,所說皆為水利事務,很可能是漢代人的手筆。而中間一段所引之令,則當是齊令。按照這里的說法,齊國是在每年末、秋收之后,省視境內的百姓,檢查、登記每家的人口與田地(“案家人比地”),編排、確定什家、五家的互保組織,分別登記民戶的男、女與大、小。
那些年老不能再勞動、服役的,就免除其戶籍編排;有較重疾病也不能從事勞作的,在戶籍簿上特別注明“疾”字,暫時免除其徭役;雖然有疾病但仍然可以從事較輕勞作的,減免一半的勞役。在這一過程中,也要確定可以征發服兵役、做甲士的名單、數額,并將其名籍報告到“都”這一級(應當指各邑的大夫)。“都”要親自檢查相關資料,如果發現還有未如實上報、或上報信息不夠全面的(“余、不足之處”),就立即向“水官”(疑為“本官”之訛誤,當即“本管”,意為直接負責的官吏)下達命令。
“水官”(本管)再根據“都”所要求的應當服兵役的甲士數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等一起,直接到“里”中去檢查,逐一詢問各家的父母,對照籍簿,以確保沒有遺漏(“因父母案行,閱具”)。在這里,“里”之上是“都”,應當相當于《管子·小匡》中的“連”(二百家)、“卒”(三百家)或《管子·乘馬》中的“鄉”(二百五十家)。
《管子》之書,非成于一人一時之用,而當為一家學說之總匯,向為通識。據上所考,則《管子》所述齊國鄉里制,各篇之中并不相同,大致言之,又可以別為三個系統:
一是《小匡》篇所述,與《國語·齊語》所述大致相合,其所述鄉里制,區分國、鄙,國中分置二十一鄉,實行軌—里—連—鄉四級制;鄙中分置五屬,實行邑—卒—鄉—縣—屬五級制。
二是《立政》篇與《乘馬》篇所述,可以合為一個系統:國中分為五個鄉,實行伍(什)—游—里—州—鄉五級制;鄙中分設五個屬,實行伍—連—里—鄉—都—屬六級制。
三是《度地》篇引齊令所記,見有三老、里有司、伍長、都之目,可知伍之上有“里”,“里”之上有“都”(“都”之上似又有“州”),與上述兩種制度均不能完全相合。
《管子》各篇有關鄉里控制體系的敘述相互歧異,然從這些議論中,我們仍然可以見出春秋時期齊國鄉里控制體系的一些基本方面:第一,春秋初年,齊桓、管仲改革,整頓國、鄙異制的鄉里控制體系,即以軍令“制國”,在“國”中實行兵農合一制;而以政令“制鄙”,在“鄙”中分劃文政、武政之權,實行軍、民分治之制。
此種二元控制體系,當遵循周制國、野分治的基本原則,亦沿用西周以來齊國政治的基本格局。然此種國、鄙二元的控制體制,在春秋初實已松弛,齊桓、管仲整頓修復之,然其后不久,或復趨于松弛乃至崩解,故《管子·度地》中已不復分言國、鄙之制。第二,《管子》各篇及《國語·齊語》雖然對于國、鄙控制體系層級的敘述各不相同,卻大都認為軌或伍(五家)、里(五十家)或邑(三十家)乃是最基本的組織。據《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里有五十家,邑為三十家;據《管子·立政》與《管子·乘馬》,國中之制,在什伍組織之上的是游,游有五十家;鄙中之制,在什伍組織之上的是里,里各五十家;《管子·度地》不分國、鄙,什伍組織之上的是里,里有百家。無論如何,三十家、五十家到百家之間的邑、里,乃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基層管理單位,應無疑問。
第三,《管子》各篇與《國語·齊語》所說,在里、邑之上的管理層級,層級數及其名稱均相差甚大:據《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國中之制,里之上有連(二百家)、鄉(二千家)、師(一萬家),國人分置二十一鄉,共有四萬二千家;鄙中之制,邑之上有卒(三百家)、鄉(三千家)、縣(九千家)、屬(九萬家),鄙中分設五屬,故有四十五萬家。據《管子·立政》與《管子·乘馬》,國中之制,游(五十家)之上有里(五百家)、州(五千家)、鄉(二萬五千家),國人分設五鄉,故有十二萬五千家;鄙中之制,里(五十家)之上有鄉(二百五十家)、都(千家)。
《管子·度地》不分國、鄙,里(百家)之上有術(千家)、州(萬家)、都(十萬家)。千家(二千家、三千家、五千家)以上的管理單位,實屬于較高層級的軍政管理單位,姑且不論,而較五十家(或百家)之里更高一級的管理單位,則主要有連(二百家)、卒(三百家)、鄉(二百五十家)、里(五百家)四種名目。此四種名目,都應當是包括若干三五十家之“里”、“邑”的地域性管理單位。簡言之,春秋時期齊國的鄉里控制體系,大抵由軌、里(邑)、鄉三級組成:最基層的一級是由五家組成的軌或伍,第二級是三十家、五十家乃至百家不等的里(或邑),第三級是二百家至五百家不等的連、卒、鄉或里,特別是由二百五十家組成的“鄉”。
二、陶文所見戰國時期齊地的城鄉控制體系
陶文是指刻劃、書寫或打印在陶器上文字。其中,臨淄等地出土陶文,年代集中于戰國時期,頗可見出齊國的城鄉控制狀況。據陶文資料,戰國時期齊地的城鄉控制制度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臨淄城內的“閭—里”制;二是鄉村地區的“卒—[敀]—鄉—里”制。
三、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鄉里控制的基本結構及其變化
據上引春秋晚期金文“城陽辛成里戈”和“平陽高馬里戈”,可知春秋晚期齊地應當實行邑(或鄉)—里二級制。根據齊地所出陶文資料,可知戰國時期齊國的基層管理組織,無論城鄉,大抵以二級制為主:在城中分區委派王孫公族“立事”(治事),各領有若干里;在城外的鄉村地區,則劃分各鄉,鄉各領里。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1)在今見陶文中,臨淄城內各區(內郭、華門、平門內、昌齊、者)所轄之里,皆稱為“左里”或“南左里”。齊地所出陶文中,另見有“右里敀銘”(《陶文圖錄》2.24.4,2.25.1)。雖然無法確定其“右里”屬臨淄城內的何區,但至少說明“右里”是存在的。那么,臨淄城內各區至少會劃分為左、右里。上引陶文中,高閭之下見有里、豆里等。這種制度,與《管子·小匡》《國語·齊語》所述“制國”的軌—里—連—鄉之制并不相合,但“里”作為臨淄城內的基本居民編排組織與管理單位,卻是一致的。這說明春秋以來以迄于戰國時期,臨淄城內的“里”一直是相對穩定的管理單位。同時,雖然無法判斷內郭、華門、平門內、昌齊、者、高閭等臨淄城內的各區分別包含多少“里”,但在“里”之上,存在著更高層級的地域性管理單位,卻是可以肯定的。
(2)在今見陶文中,臨淄城外的南郭鄉領有南得里,左南郭鄉領有辛里,楚郭鄉領有關里、里、里、芮里、北里、□里、藘里、而里;陶鄉領有戟里、□陽里、上□里、南□里、東□里、蒦南里、大里、中里、東里以及大蒦里、中蒦里、東蒦里等(蒦似乎后來單列為一鄉,故有蒦里、蒦楊里、蒦蔖左里、蒦魚里、蒦北左里等);丘齊鄉有里、上里、下里、平里、□上里、辛里等;子鄉(或邑)有裴子里、裴里、子里、攴里等;孟常鄉有匋里;城(鄉)有辛城里、里、□岳里、北里,鄉有榮里、尚畢里,芊鄉有辛里,黍郡鄉有戟里,思鄉有□里,膚丘鄉有武昌里,貯鄉有里,賈里鄉有匋里。
陶文所見的“里”多以制陶著稱,故各鄉所領里數當多于陶文所記,故一鄉轄里當超過五個,很可能有十個里。此種轄里的鄉,當然不會是《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所述“制國”的二千戶之鄉,以及“制鄙”的三千家之鄉,而更可能與《管子·乘馬》所記包括五個里(每里五十家)的鄉(二百五十家)相近。換言之,戰國時期齊國的鄉,當以五里二百五十家為標準。據此推測,臨淄城內的各個區,如高閭,亦大抵相當于城外的鄉,可能亦以二百五十家為標準。史稱“臨淄三百閭”③,以閭各二百五十家計,共有七萬五千家,正與所謂“臨淄之中七萬戶”相合④。
無論其戶口規模若何,閭(立事所治之區)與鄉應當是戰國時期齊國里之上的管理單位。明了此點之后,《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中所述齊桓、管仲改革時,制國為二十一鄉之“鄉”,亦當即是“閭”,是將臨淄城內(小城)分劃為二十一個居住區,每區居住的戶口大約亦以二百五十家為宜(每閭分為五個里,里各五十家)。
屬于齊公私臣的三官,三個市鄉(閭),三個工族(工閭),以及三虞、三衡,可能不在二十一閭之內。如果三官、三市鄉、三工族、三虞、三衡等各以三閭計算,則當時臨淄城中,當共有三十六個閭。凡此諸閭,蓋分別直屬于齊公或高氏、國氏。此三十六閭皆當處于后來的臨淄城中。
作者:魯西奇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