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海子詩中的自然史觀
時(shí)間:2022年01月14日 分類: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摘要】 海子的一部分短詩如《活在珍貴的人間》《歷史》和《重建家園》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本雅明談到的“自然史”的觀念。 本雅明反對宗教的救贖歷史觀,試圖將人類社會重新放到自然中去,客觀地重新認(rèn)識世界歷史進(jìn)程,尋覓并書寫一個(gè)自然發(fā)展的而非主觀臆斷的歷史。 海子在他的詩歌中賦予了人類與自然物同等的性質(zhì),他書寫的歷史是在其自然史觀的指導(dǎo)下重寫的歷史,他眼中的家園是人類與自然和解之后重建的家園。 詩人在此推翻了人類的優(yōu)越性和存在物的等級觀念,摒棄了在“人類中心主義”主導(dǎo)之下的陳舊的歷史觀念。
【關(guān)鍵詞】 海子; 詩歌; 自然史觀; 歷史; 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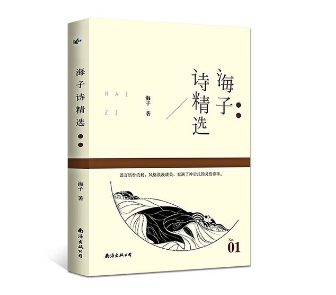
海子的詩無論是基本主題還是常用意象都與自然息息相關(guān),而他自己也是一位將其獨(dú)特的生命體驗(yàn)與自然融合在一起的詩人。 在海子的詩里能隱約看到詩歌背后的與本雅明所謂“自然史”相合的觀念:詩人把人的歷史放在廣闊的大自然的發(fā)展變化之中,賦予了人類與自然物同等的性質(zhì),他(它)們一起出生,一起長大,一起存在于世間。 海子書寫的歷史是在其自然史觀的指導(dǎo)下重寫的歷史,他眼中的家園是人類與自然和解之后重建的家園。 他捧出一顆熱切的心,希望“活在珍貴的人間”,在這樣的人間,“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 人與自然不再對立,人也不再具有物種的特殊性,如同自然界中的植物那般,與世界萬物都是平等的。 詩人在此推翻了人類的優(yōu)越性和存在物的等級觀念,也摒棄了“大人類中心主義”。 他的自然史觀鮮明地體現(xiàn)在《活在珍貴的人間》《歷史》和《重建家園》三首詩里,本文將對這三首詩進(jìn)行文本細(xì)讀,釋放出其中隱含著的詩人的獨(dú)到探索。
一、有關(guān)“自然史”的概念辨析
人類從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時(shí)代走出來以后,就與自然漸行漸遠(yuǎn),而著力打造屬于人的第二世界,發(fā)明出很多自然界本來沒有的東西。 這第二世界里,自然界本來沒有的事物當(dāng)然也包括各種各樣的意識形式,隨著人類社會發(fā)展壯大,人們的精神文明越來越豐富多彩、紛繁復(fù)雜。 在意識和思想領(lǐng)域,人與自然有了最大程度的分離,自然仿佛是一個(gè)龐大的、陌生的、需要馴服的對象。 但是在美學(xué)領(lǐng)域,一些人仍保持著對自然的熟悉和親近,試圖重新引入自然來對人類行為糾偏,以此喚醒人們另一種思考模式。
(一)“自然史”提出的背景
從人類歷史逐漸走向現(xiàn)代,孜孜不倦地追求“現(xiàn)代性”開始,與自然的分離便不可避免了,直到今天某種固有觀念仍在生效。 人們喊著“戰(zhàn)勝自然、征服自然”的口號,懷抱著“人定勝天”的信心,激昂地建設(shè)人造世界,也在這個(gè)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將自身與自然之間劃出一條界線。 “資產(chǎn)階級文明在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前人所不可想象的物質(zhì)、文化財(cái)富的同時(shí),也把人放在了自然的對立面。 ” ①資本主義迅猛發(fā)展,在物質(zhì)層面對自然的索取和破壞自不待言,但在意識層面,人和自然的對立則更為深刻。 人一旦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力量,發(fā)現(xiàn)自己能夠認(rèn)識世界、改造世界,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去自由創(chuàng)造自然界不能給予的所有,就會相信人的獨(dú)立價(jià)值、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shí)也會格外凸顯人類的地位,甚至一度認(rèn)為自己是萬物的主宰。 當(dāng)人的主體性、所謂的“自我”不斷膨脹,看待自然時(shí)就不會采用平視的目光,而是一切都從自己出發(fā),從內(nèi)心出發(fā),即使偶爾向自然投去關(guān)切的一瞥,也是為了證明一個(gè)偉大而優(yōu)越的“我”的對象化的能力。 浪漫主義便是如此,歷史上沒有什么比它更加注重“自我”,注重人的主體意識,同時(shí)也那樣看重自然、熱愛自然乃至崇拜自然。 而它蓬勃興盛的時(shí)代也是資本主義迅疾生長的時(shí)代。 浪漫主義者對自然的感情,最終也成為其內(nèi)在性、其主觀意志的漂亮的裝飾物和華麗動人的注腳。 浪漫主義代表人物盧梭與其說充滿深情地贊頌一棵樹,不如說他寧愿自己變成一棵樹,盡興地發(fā)揮想象力做一個(gè)“白日夢”,似乎在夢里人能夠與外在的自然完美融合。 當(dāng)浪漫主義者在生活中遇到坎坷和挫折,他們就會哀傷地“回歸”自然,仿佛在那里找到了慰藉。 “自然似乎是一種完美友誼,而這種友誼的程度與她沒被人污染的程度恰成正比。 ” ②
浪漫主義者也許把自然當(dāng)成了知音,當(dāng)成了可以供他們傾訴心事的朋友,而他們向往的東西正是自然的那種未受到人的影響和改變或曰“污染”的純潔性、天然性。 白璧德在論述浪漫主義時(shí),看到了其自然崇拜里面深藏的內(nèi)在虛偽性——它的偽精神性和偽宗教性。 浪漫主義者對自然的崇拜具有高度的精神性,有著一股類似于宗教的神圣感覺和為之獻(xiàn)身的沖動、激情。 但白璧德尖銳地指出,“因?yàn)槔寺髁x者感興趣的內(nèi)在生活并不是他與別人共有的內(nèi)在生活,而是他自己最獨(dú)特的個(gè)人感情——簡言之,就是他的情緒。 人們準(zhǔn)備歡迎的隱喻和象征不是表達(dá)某種多少個(gè)人化的東西,而是與他們的共同性相關(guān)。 ” ③也就是說,浪漫主義者永遠(yuǎn)要回到自己的內(nèi)心,他們重視自然,最終也是為了表達(dá)和發(fā)泄自己的情緒。 他們把自然變成其情緒的玩物,與自然對話實(shí)際上只是在和自己的情緒交往。 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根本沒有適應(yīng)自然、理解自然,也不愿與自然平等交流。 那些貼近自然的美妙詩句都是他們的想象,他們自編自演的白日夢,那些對自然的親近和崇拜的語詞也是自我主義的產(chǎn)物。 由此來看,浪漫主義的自然觀雖然擺脫了資本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庸俗利己主義和理性主義指導(dǎo)下的精致利己主義,但它也是一種利己主義,只不過更加委婉,也更加隱蔽含混。 浪漫主義高調(diào)宣揚(yáng)人的主體性,即使并未有意地為資本主義的進(jìn)取精神煽風(fēng)點(diǎn)火,仍然加深了人和自然之間的鴻溝——主客體的界線愈來愈鮮明清晰,其等級秩序也牢不可破(人類處于高位,自然只是等待著被人們利用)。 當(dāng)“人”的形象被成功地確立,越來越高大偉岸,“自然”就被淡化,越來越模糊,成為虛幻的襯托背景。
(二)本雅明的“自然史”
本雅明看到了發(fā)達(dá)資本主義時(shí)代人與自然的隔離和對立,也看到了人類越發(fā)強(qiáng)大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弊端。 他的“自然史”概念試圖將人類社會重新放到自然中去,成為自然的有機(jī)組成部分。 最初,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一書里提出“自然的歷史”,主要針對人們自造的“救贖歷史”。 他看到,“基督教編年史是將歷史進(jìn)程的整體,即世界歷史進(jìn)程表現(xiàn)為一個(gè)救贖歷史進(jìn)程。 ” ④基督教把世界歷史進(jìn)程書寫成“人有原罪——尋求救贖、努力贖罪——獲得拯救”這樣一個(gè)過程,這種歷史觀絲毫不顧及自然歷史是如何發(fā)展、如何呈現(xiàn)自身的,而用一個(gè)不經(jīng)論證的幻想來描繪歷史進(jìn)程。 基督教編年史屬于目的論式的歷史觀,所謂目的也是人們強(qiáng)加的目的,它集中體現(xiàn)了看待世界時(shí)人的自以為是,人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慣性。
但本雅明想用“自然史”對抗救贖歷史,試圖客觀地重新認(rèn)識世界歷史進(jìn)程,回到歷史情境之中,尋覓并書寫一個(gè)自然發(fā)展的而非主觀臆斷的歷史。 他的“自然史”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大自然的歷史,其實(shí)他所說的自然史“在自然的進(jìn)程中看到人的因素,也在技術(shù)、社會、文化的進(jìn)程中看到自然的因素……在此,主體和客體互相包容、互相占有,而非彼此排斥。 歷史作為‘人化的自然’,而自然作為‘自在的歷史’,都在對方的存在中看到了自己的‘合目的性’。 ” ⑤因此,人類和自然之間的巨大鴻溝被填平了,人和自然的等級秩序也瓦解了,二者獲得了全新意義的平等,而且產(chǎn)生了良性互動。 在“自然史”的觀念里,人類中心主義的話語漸漸消退,世界歷史就是那樣自然地發(fā)展著,并不是為了某種救贖,也不會因?yàn)榈玫搅司融H而終結(jié)。 這樣一來,人類與自然物就沒有高下之分,自然也不是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人們就能更客觀更中立地看待自身,尊重其他自然物,謙虛地生存在整體的自然中。
叔本華曾說,文學(xué)中的主題分為真實(shí)的自然的主題和人造的想象的主題,那么,書寫的歷史也可分為自然的歷史和人為斷想的歷史。 支撐海子詩歌的歷史觀念是類似于本雅明所謂的自然史觀。 詩人在自己的詩里將人和自然物放到平等的位置上,沒有夸大人類的能力,也沒有采用人們自封的“宏大敘事”所習(xí)慣使用的表現(xiàn)方法,而是心平氣和地看看人,再看看自然,并流露出他心中的愛與希望。
二、海子詩歌中的自然史觀
海子的詩歌喜歡將一切都自然化,如本屬于人類社會的宏大命題歷史和死亡等等。 他的“自然化”給詩歌染上了一絲神秘色彩,似乎總有一些啟示若隱若現(xiàn)。 他的詩也因?yàn)樵姼璞澈蟮淖匀皇酚^而多次把屬于人的生命情境和“無知無覺”的自然物相對應(yīng),這看起來很像“象征”手法,但其實(shí)是獨(dú)特觀念的作用。 海子沒有像浪漫主義詩人那樣一心顧著自己的個(gè)人感情,他的詩是向自然打開的,如一個(g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烏托邦。 海子不加區(qū)分地寫人和自然,他的詩歌中,自然像人,人像自然,人與自然中的物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
(一)海子心目中的“歷史”
提及“歷史”,人們腦海中頓時(shí)會涌現(xiàn)出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或重要的歷史學(xué)說。 但海子的詩《歷史》,卻寫得輕盈而虛渺。 “我們的嘴唇第一次擁有/藍(lán)色的水/盛滿陶罐/還有十幾只南方的星辰” ⑥,這一句只用原始人手作陶罐、盛水來喝的細(xì)節(jié)便勾畫出對人類社會開端的景象,藍(lán)色的水和南方的星辰都是自然物,而它們滋養(yǎng)了人的肉體,又給人帶來精神的啟發(fā)。 “火種/最初憂傷的別離”,發(fā)現(xiàn)火、使用火是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gè)里程碑,但海子卻說這是“憂傷的別離”——它確實(shí)是人和自然分離的起點(diǎn),自從人類能夠利用火來改善生存環(huán)境,促進(jìn)生產(chǎn),人就和自然慢慢分開,可這是不能避免的進(jìn)步。 火的意象代表了一切科學(xué)技術(shù),它們使人走出蠻荒,也開始將自然放到被掠奪的位置上。 “你是穿黑色夜服的人/在野地里發(fā)現(xiàn)第一枝植物/腳插進(jìn)土地/再也拔不出”,人們的祖先曾經(jīng)在黑暗中摸索,好似穿著黑色夜服的人,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可供人類改造的農(nóng)作物,而這又是自然歷史饋贈給人們的。 農(nóng)耕文明的到來就伴隨著許許多多不經(jīng)意間的發(fā)現(xiàn)。 春天想親吻大地,帶來復(fù)蘇的氣息,只好讓“那些寂寞的花朵”充當(dāng)她“遺失的嘴唇”。 “公元前我們太小/公元后我們又太老/沒有人見到那一次真正美麗的微笑”,早期的人類極度依賴自然而生存,像孩子一樣弱小無助,并沒有很好地理解自然,可一旦掌握了自主創(chuàng)造的能力,便很快拋開了對自然的尊敬,自鳴得意地凌駕其上,所以人們從未達(dá)成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標(biāo),“真正美麗的微笑”或許指雙方互相尊重的良性關(guān)系。 當(dāng)詩人“舉手敲門”,準(zhǔn)備叩問歷史,探詢歷史的奧秘,“帶來的象形文字撒落一地”,他感到文字所記錄的歷史的不足,甚至是虛妄。 但沒有這些記錄,歷史到何處追尋? 它該用什么方式呈現(xiàn)? 人們說“文本之外無歷史”,拋棄了文字記載,歷史也同時(shí)消失了。 在這里海子只是想表明他在懷疑人類書寫的帶著強(qiáng)烈自我中心主義氣息的歷史,而推崇“自然的歷史”。 欲求得這種歷史,“我緩緩摘下帽子”,褪去一切由人賦予的外在意義,“靠著我愛的人/合上眼睛”。 歷史化為“一座古老的銅像”,而歷史中數(shù)不勝數(shù)的血淚代價(jià)和掙扎犧牲是“青銅浸透了淚水”,海子重視那些過程中的付出,并紀(jì)念人們的投入,這是目的論歷史觀容易忽視的細(xì)節(jié)——目的論歷史觀更看重結(jié)果,更多注意進(jìn)化論式的“進(jìn)步”:只要明天會更好,曾經(jīng)的犧牲無足輕重。 在此,海子的《歷史》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自然史觀。
(二)“家園”怎樣重建
海子的《重建家園》深刻地表明,人應(yīng)放棄自以為是的優(yōu)越感,用一顆懷有敬畏的心,換一種眼光重新理解人類自身和自然的關(guān)系。 所以詩人才會在詩中表達(dá)那么多次“放棄智慧”“放棄沉思”,愿“大地自己呈現(xiàn)”。 “放棄智慧/停止仰望長空”,停止人類對自身歷史進(jìn)程的想象與附加在世界歷史進(jìn)程之上的論斷,其實(shí)就是放棄那些不切實(shí)際的空想和唯我獨(dú)尊的進(jìn)行意義給予的權(quán)力。 因此“為了生成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來澆灌家鄉(xiāng)平靜的果園”。 海子設(shè)想家園的意象為果園,這是能夠給人美好的回報(bào)(果子)卻又需要勞作才能有產(chǎn)出的園地。 “生成無須洞察/大地自己呈現(xiàn)”,家園的建設(shè)其實(shí)是按照自然的規(guī)律來完成的,洞察、分析、研究和判斷并沒那么重要,也就是說,太過主觀往往遠(yuǎn)離真正的家園,大地(自然)早已規(guī)定了一切。 重建家園這個(gè)過程里有幸福也有痛苦,但這幸福與痛苦都在自然的歷史中展開,并不符合人們言說的某個(gè)目的(例如救贖)。 海子一遍遍強(qiáng)調(diào)“放棄沉思和智慧”,因?yàn)?ldquo;如果不能帶來麥粒”,就“請對誠實(shí)的大地保持緘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沉思和智慧也許代表理性,它很可能無法給人們帶來意料中的收獲,過度使用理性反而有害,當(dāng)主體性的膨脹具體體現(xiàn)為資本主義的無限擴(kuò)張時(shí),它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災(zāi)難。 海子希望人們對誠實(shí)的大地(播種什么就收獲什么,故曰誠實(shí))保持沉默,不要過多地干擾自然規(guī)律,應(yīng)該順應(yīng)自然本性。 “風(fēng)吹炊煙/果園就在我的身旁靜靜叫喊”,這一句描繪出一幅樸素靜美的田園風(fēng)景畫,炊煙代表人間煙火氣,果園的叫喊是樹葉在風(fēng)中嘩嘩作響,這是人和自然達(dá)至和諧狀態(tài)的閑適家園。 最后一句“雙手勞動/慰藉心靈”,表現(xiàn)了海子對勞動的重新認(rèn)識,他認(rèn)可勞動,熱愛勞動,人們用自己的雙手進(jìn)行現(xiàn)實(shí)的勞動才能建設(shè)家園,同時(shí)得到精神的滿足,慰藉心靈。
(三)人間的幸福
海子追求現(xiàn)世幸福,的確,他向往超越性的夢境,但實(shí)際上他并不把幸福寄托到“來世”,他的自然史觀讓他否定救贖歷史觀,現(xiàn)世的自然的歷史才是他認(rèn)可的。 他用《活在珍貴的人間》充滿真情地表達(dá)他的愛與祝福。 他熱愛自然物,熱愛強(qiáng)烈的太陽,溫柔的水波,一層層覆蓋著的白云。 “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徹底干凈的黑土塊”,黑土塊干凈是指它純凈無污染的天然樣貌,而它又是肥沃的,是自然界草木繁盛、生機(jī)勃勃的保證。 在這里,人變成了黑土塊,徹底與自然融為一體。 所以詩人熱烈贊頌“活在這珍貴的人間/泥土高濺,撲打面頰”,而不是嫌棄泥土的骯臟和低賤。 一些高傲的人遠(yuǎn)離泥土,盡可能地清除它,但海子認(rèn)為,人和泥土并沒有等級之分,泥土養(yǎng)育了生命,它本應(yīng)享受榮耀。 人和自然分離之日,二者的等級就已確定,無論是浪漫主義動情的歌頌,還是科學(xué)主義不遺余力的利用,都明確了人的優(yōu)先和高位。 堅(jiān)持自然史,也就是在顛覆這種觀念,將人類放到自然中,與其他自然物平等對話。 海子所謂的“珍貴的人間”,就是這樣的情況:“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愛情和雨水一樣幸福。 ”人類、愛情都是人的世界里至關(guān)重要的,現(xiàn)在人類如同植物,都植根于大地,自由地存在著,愛情如雨水一般促進(jìn)萬物生長、后代繁榮永續(xù),可見海子拉平了人類與自然物的地位,這是他的自然史觀中最核心部分的體現(xiàn)。
注釋:
①⑤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9頁,第9頁。
②③白璧德著,孫宜學(xué)譯:《盧梭與浪漫主義》,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第264頁,第281頁。
④本雅明著,李雙志、蘇偉譯:《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
⑥海子著,西川編:《海子詩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參考文獻(xiàn):
[1](德)瓦爾特·本雅明著,(德)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M].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9.
[2](美)歐文·白璧德.盧梭與浪漫主義[M].孫宜學(xué)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
[3](德)瓦爾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M].李雙志,蘇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1.
[4]海子著,西川編.海子詩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作者簡介:邢玉丹,女,漢族,黑龍江鶴崗人,北京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系博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
SCI期刊目錄
熱門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fù)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fù)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yī)學(xué)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yè)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qū)和影響
- 2025-02-10經(jīng)管專業(yè)快速發(fā)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fā)論文,解答及指導(dǎo)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fā)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shù)據(jù)庫?scopus數(shù)據(jù)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fù)合材料科學(xué)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jié)能領(lǐng)域論文選題31個(gè),
- 2025-03-28電子技術(shù)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xiàn)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fā)表的論文文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