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平等哲學下對我國農民工“健康移民效應”的再考察
時間:2022年04月20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摘 要:“健康移民效應”是指相比于本地居民,移民的健康狀況更好。本文使用 RUMiC 2008和 2009 數據,發現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比城市居民更差。為剖析我國現實與“健康移民效應”這一典型事實相矛盾的原因,本文將“機會平等”哲學理念與“健康移民效應”相結合,在新構建的框架下進行了分解研究,結果顯示: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應”來看,外出農民工本該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即我國農民工的“健康移民效應”本該存在,但嚴重的機會不平等拉低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終導致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 值大了 0.112)。此外,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好于從未外出的農村居民,也好于回流的農民工,這表明農民工的外出和回流存在“自選擇”機制。但這些自選擇機制主要是合理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機會的不平等。
關鍵詞:健康移民效應;機會平等;心理健康;農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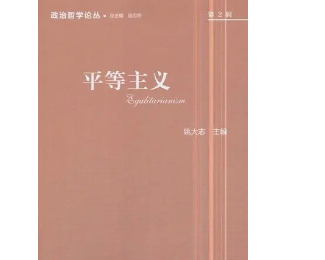
一、引 言
公共衛生領域有一大特征事實被稱為“健康移民效應”(Healthy Immigrant Effect,簡稱 HIE),具體是指和當地居民相比,移民的健康狀況平均來看反而更好(Antecol and Bedard,2015)①。有關 HIE 的證據,近年來在國際移民文獻中已被大量實證研究證實②。在我國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以移民方式進城務工。據《2016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6 年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 28 171 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高達 16 934 萬人③。
外出農民工的健康問題不僅關乎這一龐大群體自身的福利,而且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這對城鄉的經濟發展和減貧都有重要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學者開始借鑒 HIE 的思路來研究中國國內移民(外出農民工)的健康問題。他們使用了不同的主觀與客觀衡量身體健康的指標和不同的數據,發現外出農民工普遍比城市居民更健康,即證實在中國城市,也存在“健康移民效應”(如Tong & Piotrowski,2012;牛建林,2013;周小剛和陸銘,2016)。但上述研究均局限在自評健康或客觀生理健康方面,對于外出農民工的心理狀況涉及較少。
直覺上,自評健康和生理健康上存在 HIE 比較符合邏輯,因為大多自我感覺健康或者身強力壯的農民才會外出務工。然而,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 HIE 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因為外出農民工來到陌生的城市,缺少親人的陪伴,通常從事更低級的工作,受到本地人的歧視,即便生理上更健康,心理上也可能更焦慮、更壓抑。在為數不多的有關中國心理健康的 HIE 文獻中,Wen et al.(2010)通過分析上海市調研數據發現存在 HIE;而 Chen(2011)通過分析北京市調研數據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因此,相比于自評健康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上的 HIE 更是一個有待實證檢驗的問題。本文將采用覆蓋面更廣的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城鄉移民調查(RUMiC)2008 和 2009 兩年的數據,對我國城市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分析,實證驗證是否存在“健康移民效應”。這是本研究選擇以心理健康作為切入點的一大原因。然而,RUMiC 數據顯示,農民工平均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比本地人更差,似乎我們得到了與國際主流文獻相悖的結論。
但我國農民工與本地人有著巨大的分割(disparities):在現實中,他們往往在城市中從事著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更臟、更危險、更累的(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工作,勞動時間更長、強度更大。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和居住條件很差,遠離家鄉,難以得到親戚和朋友的支持。再加上我國戶籍分割的醫保制度,使農民工在醫療保障方面也處于不利的地位。這些因素都損害了農民工的身體健康。
也就是農民工與本地居民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存在著巨大的錯配,僅僅比較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健康水平可能不能反映出“健康移民效應”的本質。而當我們在回歸中加入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地位等一系列 HIE 文獻中“常規”控制變量后,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更好。據我們所知,目前 HIE 文獻中還未曾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么到底存在不存在 HIE 呢?我們認為,這恰恰體現了中國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問題可能更加復雜。簡單地驗證是否存在“健康移民效應”并不足以完全解釋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挖掘出隱藏在這一現象背后的機制會更有意義。而之前研究的實證方法和分析框架,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借助機會平等理論(Equality of Opportunity,簡稱 EOP)對這一現象背后的機制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分析。機會平等理念源于政治哲學,Roemer(1998)用數理方式將其引入經濟學,專門探討表面不平等背后的實質不公平問題。簡而言之,造成個體“優勢”不平等的因素可分為兩類,將不可控的因素稱為“環境”,將可控因素稱為“努力”。由“環境”因素導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由“努力”因素導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
同等“努力”,無論處在哪種“環境”下,都應該獲得同等“優勢”,否則就是機會的不平等。健康的不平等同樣存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兩類機制,因此近年來,EOP 理論越來越多地在健康經濟學中使用(Roemer and Trannoy,2016)。HIE 描述的是外出農民工與本地居民存在心理健康上的不平等現象,這個不平等背后同樣存在合理與不合理的兩類機制,當我們將 EOP 理論與 HIE 現象結合起來就發現,正是由于這兩類不同機制的存在,才出現了上述描述統計與回歸結果矛盾的現象。
本文的具體結論如下: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應”來看,外出農民工本該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也就是說“健康移民效應”本該存在。但嚴重的機會不平等拉低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終導致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值大了 0.112),掩蓋甚至逆轉了“健康移民效應”。這本質上反映了由于戶籍分割所帶來的嚴重的健康不公平。機制方面,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從未外出的農村居民,也好于回流務工人員,這反映了外出和回流的自選擇效應,究其原因,主要是合理的“努力特征效應”,而不是機會不平等。這一發現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全球約有 25%的人一生中會遭遇到心理疾病(Aglipay et al.,2013)。有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疾病譜正在發生變化:非傳染性疾病超過傳染性疾病成為造成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心理健康問題在中國越來越普遍(Lu et al.,2012),對勞動收入、個人就業都會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張曉明等,2021)。一些社會學文獻還表明,心理健康因素決定了外出農民工是否愿意長住城市,外出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的最高形式是心理層面的健康融合(楊菊華,2015;崔巖,2012)。綜上,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
第一,“健康移民效應”只是“描述了”移民與本地人健康差異的現象,本身不夠深刻。與現階段大多數 HIE 文獻僅采用回歸分析(OLS、Logit、Probit 等)方法相比,本文將 EOP 理論與 HIE 相結合,在回歸分析的基礎上,借鑒勞動經濟學的分解方法,挖掘出隱藏在 HIE 背后的東西,從而得到了一般 HIE 文獻和研究方法所不能提供的重要結論,也為HIE 這一支文獻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
第二,如前文所述,對農民工心理健康進行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義,而本文為 HIE 文獻提供了來自心理健康方面的證據。第三,本文所使用的 RUMiC 數據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包含城市本地人樣本、外出農民工樣本以及農村居民樣本。
本文采用合理標準,從農村樣本中劃分了從未外出農民、已回流農民和正在外出農民,從而不僅分析 HIE 本身,還分析了 HIE 的自選擇機制和回流機制。與大多數 HIE 文獻相比,本文顯得更加詳細和全面。第四,EOP 理論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健康中,但有關中國健康機會不平等的文獻非常少,本文也為健康EOP 這支文獻提供了來自中國外出農民工的證據。
二、文獻回顧
(一)健康移民效應
(1)從國際 HIE 到國內 HIE如引言所述,在國際移民的 HIE 方面已有大量研究。多數研究均證實了 HIE 的存在(可參見腳注 2)。相比而言,借用 HIE 思路研究國內移民問題的較少。Lu(2008)對印度尼西亞農村遷往城市的移民健康進行研究,開創性地把 HIE 引入國內移民健康效應,他發現印尼國內 HIE 的結論較為復雜,隨著遷移類型和年齡的不同而不同。此后,Lu(2010)繼續用印尼 1997-2000 年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生理健康方面沒有 YSM 效應,在心理健康上存在 YSM 效應。隨后,一些中國學者也引入 HIE 研究國內外出農民工問題。如 Tong and Piotrowski(2012)、牛建林(2013)、周小剛和陸銘(2016)均發現我國外出農民工的健康狀況好于當地人,即存在 HIE現象。相比于自評健康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 HIE 文獻要少一些。
Alegria et al.(2008)和 Cook etal.(2009)發現在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s)方面,拉美裔移民的健康水平要好于當地美國人,即存在 HIE。類似的,Menezes et al.(2011)和 Aglipay et al.(2013)用加拿大數據,分別以精神疾病和焦慮感(anxiety disorders)作為心理健康的代理變量,均證實加拿大存在 HIE。Rivera etal.(2016)用了綜合性的心理健康指標(GHQ-12 量表),發現移入時間少于 10 年的西班牙移民心理健康水平更好。他們還發現,移入時間大于 10 年的移民群體則沒有 HIE,從而也驗證了 YSM的存在。
Bergeron et al.(2009)發現加拿大移民由于文化、語言、氣候等原因,來到加拿大之后心理上變得更脆弱。Straiton et al.(2014)也發現澳大利亞的男性非英語國家的移民,隨著移入時間的推移患有心理健康疾病的概率顯著增加。這些研究驗證了心理健康上的YSM 效應。如前文所述,關于中國心理健康方面的 HIE 研究相對缺乏,Wen et al.(2010)和 Chen(2011)分別用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數據,得到了相反的 HIE 證據。
因此,本研究試圖利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深入分析我國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上的 HIE。如前文所述,我國 HIE 的研究大多是自評健康和生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證據和機制可能完全不一樣,結論也更復雜。考慮到 YSM 是對 HIE 結論的延伸,我國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上的 HIE本身就有一系列問題亟待討論。因此,本研究擬結合 EOP 理論,用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單獨細化 HIE 問題,而對 YSM 不再做過多闡述。(2)HIE 的機制上文簡單敘述了 HIE 相關研究的結論。從 HIE 存在的原因來看,大致有以下三個機制(Chen,2011):第一,移民自選擇效應。一般身體較好的人才會選擇移民,因此,移民群體的身體狀況平均而言會更好(Frisbie et al.,2001;McDonald and Kennedy,2004)。
這個機制同樣可以解釋中國國內外出農民工的 HIE,通常身強力壯的農村居民才會選擇外出務工(周小剛和陸銘,2016)。在國際移民的選擇問題中,還存在一個機制:移民去向國通常會有移民審查程序(immigration screeningprocess),將一些身體較差的篩選出去。在我國國內外出農民工的 HIE 問題中,這個機制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國內移民并沒有這樣的審核程序。但國內大城市通常會有嚴格的落戶政策,只有條件較好的農民工才有可能落戶大城市,因此身體較差的農民工可能已經返鄉。這實際上是 HIE 的第二個機制——回流效應。第二,回流效應(salmon effect)。
一般身體較差的移民會返回來源國,因此去向國移民群體的平均身體狀況就會更好。例如 Fong(2008)發現在英國和愛爾蘭的中國移民會因為健康問題返回中國。不過這一機制的實證結論并不明確,也有一些反例。如 Van Hook and Zhang(2011)發現在美國,健康并不是返鄉的決定性因素。從直覺上講,回流效應也可以解釋我國外出農民工的 HIE問題:回鄉的農民工身體狀況差(牛建林,2013)。外出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奉獻了才智和健康,但當他們的健康下降之后,城市卻沒有接納他們,而是將他們推回了農村(周小剛和陸銘,2016)。
第三,醫療可及性。有研究表明,移民醫療服務利用少,對自身疾病信息不夠了解,所以會高估自己的健康狀況(McDonald and Kennedy,2004),從而在主觀健康指標方面造成對 HIE 的高估。但同樣,該機制的實證結論并不明確,因為也有研究表明增加醫療服務利用可以有效提高健康水平,移民普遍擁有更少的醫療服務利用,因此醫療可及性會是減少 HIE 的因素(Read and Reynolds,2012)。所以,醫療因素對 HIE 的作用在符號上難以確定(Antecol and Bedard,2015)。本文將分別對上述三個機制進行分析。
三、方法、數據與變量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城鄉移民調查”(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RUMiC),該數據采用分層結合隨機地圖分塊抽樣方法,對中國 10 個省的 15 個大中城市中的 5 000 個外來移民家庭進行詳細的調查,獲得了包括外來移民的個人及家庭在工作、收入、消費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詳細的信息②。除了移民的信息之外,該調查還通過國家統計局的入戶調查獲得了上述 15 個城市的 5 000 戶城市居民和相應 10 個省份的 8 000 戶農村居民的樣本。
因此,RUMiC 包含移民、城鎮住戶和農村住戶三個數據集。我們具體使用了 2008 和 2009 年(分別反映樣本 2007 年和 2008 年情況)兩年的 RUMiC 混合截面數據。本文通過對比移民和城鎮住戶這兩個數據集,以度量 HIE。同時,為了補充分析外出自選擇機制和回流機制,我們還使用了農村住戶數據集。由于 RUMiC 的農村住戶數據集中包含了如下三部分群體:
(1)從來沒有任何移民經歷、一直生活在農村的居民;(2)回流的移民:過去有移民經歷但本年度生活在農村;(3)本年度有外出經歷但調研時在農村的農村居民。所以按照對應的標準,我們將農村數據詳細分成上述三類,分別代表:從未外出農村居民、回流農民和農村外出農民工。通過對比從未外出農村居民和農村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考察外出自選擇機制;對比回流農民和農村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考察回流機制③。采用本數據的主要優點在于:
(1)RUMiC 是一套專門針對移民的數據,非常符合本研究主旨。(2)在抽樣方法上與以往類似的調查不同,本研究采用了以農民工工作地點(而不是居住地點)為核心來確定抽樣框,再輔以地圖分塊的抽樣方法。因此得以將以往眾多調查中所遺漏的居住在工作地點的大量農民工納入抽樣框。
(3)該數據具有全國代表性,除包含城市本地人樣本和外出農民工樣本外,還有豐富的農村住戶數據集,這樣不僅可以分析 HIE 本身,還可以分析 HIE 的自選擇機制和回流機制,因此和大多數 HIE 文獻相比,本文分析可以更加全面。(4)具有較為詳細的心理健康測量指標。
關于心理健康的指標,相關 HIE 文獻中有用精神疾病的(如 Cook et al.,2009; Menezes etal.,2011),有用焦慮感的(如 Aglipay et al.,2013),有用心理困擾(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如 Chen,2011)。如同 Rivera et al.(2016)和 Gotsens et al.(2015)一樣,本文采用的是綜合心理健康指標 GHQ-12 量表,該量表由 12 個主觀問題組成,每題有 4 個選項,分別賦值 0、1、2、3,分值越大代表心理健康問題越大。把這 12 個得分加總,就是綜合心理健康得分①。
本文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環境”與“努力”變量的選取是本文的關鍵。在 EOP 語境下,“環境”代表那些造成健康不平等的道德上不合理的因素,反之“努力”代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因素。按照健康經濟學中水平公平的觀點,擁有同樣人口學特征的人需要對應同樣的健康水平,不能因戶籍、社會經濟地位等不同而有不同的健康水平。
因此,我們將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工作、單位所有制、規模、合同類型、行業這些反映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變量,定義為“環境”因素;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這三個人口學變量,定義為“努力”因素。這也與健康機會平等文獻中的做法一致(如 Fleurbaeyand Schokkaert,2011;馬超等,2017;馬超等,2018)。
此外,本文還加入了“是否每天吸煙”作為健康習慣的代理變量。在健康方面的 EOP 文獻中,通常將吸煙作為“努力”變量(如 Rosa Dias,2009;Trannoy et al.,2010a),因為這是個體責任,因吸煙多造成的健康水平差是“合理”的。在研究我國外出農民工問題時,這一點可能值得商榷:外出農民工本身社會經濟地位低,從事更辛勞的工作,缺乏親人關懷,更需要吸煙解悶,這么來看吸煙造成的健康損害是機會不平等的。
因為吸煙這個“努力”是由“環境”造成的,并進一步影響到了健康。這個問題在 EOP 文獻中被稱為“偏環境(partial circumstance)”效應(Roemer,1998;Ramos et al.,2015),不同的哲學觀點對此處理方式不一。例如 Roemer(1998)認為“偏環境”效應是不合理的,也是機會不平等的一部分;而 Barry(1991)則認為這是合理的。幸運的是,在后文回歸和分解中,吸煙因素對本文結果幾乎沒有影響,無論采取哪種哲學思想都不影響[這與 Jusot etal.(2013)的實證結論類似]。因此,后文不再考慮 EOP 的“偏環境”效應。
四、實證分析
在其他變量方面,男性的心理健康比女性顯著更好,考慮到外出農民工男性比例更高,那么描述統計的時候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應該有優勢才對,這或許暗示著在 HIE 背后,有著對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更為不利的因素,這也正是后文 EOP 討論的問題。年齡不顯著,心理健康與年齡關系不大,這也是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不一樣的地方。同樣,在自評健康或者生理健康的研究中,吸煙通常有顯著負面作用,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吸煙可能會起到緩解心理疾病的作用,所以不顯著。外企的心理健康更差,可能和過大的工作壓力有關。類似的,行業方面,教育業、政府和公共部門的心理健康也更差,這也與這些行業逐漸增加的工作壓力有關(如王陽,2008;Yang et al., 2019)。
同固定工相比,其他類型的合同工人心理健康顯著更差,這符合直覺。收入和教育的符號符合預期,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受教育水平會有更好的心理健康,這與 Rivera et al.(2016)的研究結論一致。這些協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并不是本文關注焦點,因此不再展開敘述。
綜上,本文發現我國外出農民工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外出自選擇效應,以及較弱的回流效應,這兩個效應主要是由合理的人口學因素導致。因此,在控制了個體特征的情況下進行回歸,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本地城市居民。但僅比較外出農民工和本地城市居民的均值時,發現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更差。究其原因,外出農民工面臨的巨大的健康機會不平等,使得本該更健康的他們反而健康均值更差。機會不平等占到表面 HIE 的 229.5%。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計算 HIE 時并不需要矯正自選擇效應和回流效應,因為 HIE 的含義是某一時點上當地移民與本地人的健康對比,HIE 所要比較的總體是當地人和已經被選擇完之后的移民,所以并不需要對自選擇行為和回流進行類似 Heckman 那樣的矯正。自選擇效應和回流效應是解釋 HIE 存在的機制,而不是需要調整的東西。事實上,幾乎所有的 HIE 文獻均是這個思路。雖然少數文獻如 Jatrana et al.(2013)、秦立建等(2014)采用了固定效應模型以消除不可觀測不隨時變的自選擇效應,苑會娜(2009)采用工具變量 3sls 矯正內生性問題,但這些文獻并不是對 HIE現象本身的直接研究,只是借用 HIE 概念研究移民對健康的因果效應,所以需要矯正。
五、結 語
“健康移民效應”HIE 是指相比于本地居民,移民的健康狀況更好。本文利用 RUMiC2008-2009數據對我國外出農民工的 HIE 效應進行分析,從描述統計中發現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比本地城市居民更差,而添加了一系列控制變量的回歸顯示外出農民工心理健康更好。為了找到這個矛盾背后的原因,本研究借鑒機會平等理論 EOP 對 HIE 進行分解,結果顯示:按照合理的“努力特征效應”來看,外出農民工本該比城市居民更健康(GHQ 值小 0.145),但嚴重的機會不平等拉低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GHQ 值大了 0.257),最終導致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反倒比城市居民更差(GHQ 值大了 0.112)。
外出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好于從未外出的農村居民,也好于回流務工人員,這反映了外出自選擇機制和回流機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合理的“努力特征效應”,而不是機會不平等。綜上可見,由戶籍分割導致的外出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間的機會不公,是造成我國健康不平等的最核心原因。本文還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本文的所有結論本質上仍是描述,并不涉及因果推斷,考察單獨的更為細致的變量如何對 HIE 產生因果影響,也是我們未來的工作之一。
2.本文的 EOP 是局部(local)EOP 而不是全局(global)EOP,局部機會的平等可能并不等于全局的機會平等(Roemerand Trannoy,2016)。也就是說,我們在計算 EOP 的時候只是局部地使用所需要對比的樣本,而不考慮整個社會發生的變化。這個問題從 Oaxaca 分解的角度來看,即 Oaxaca 式的分解一大前提假設為不涉及一般均衡,只有局部均衡(Fortin et al.,2011)。
3.從心理健康的指標來看,GHQ-12 雖然是廣泛采用的綜合性心理健康指標,但外出農民工和本地城市居民是兩類完全不一樣的群體,因此對主觀指標的評判可能會有系統性偏差。Mu(2014)用 Charls 數據發現我國不同地區的老年居民在匯報自評健康時有系統性差異。此外,RUMiC 問卷中只有醫療信息,而不含專門的心理方面的醫療信息。
4.由于本研究不是面板數據,因此無法嚴格考察動態的 YSM 效應,也無法考量 HIE原因中諸如過早死亡(die prematurely,Antecol and Bedard,2015)這樣的機制。這些不足之處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展望,需要將來進一步詳細研究。
參考文獻
[1] 崔巖,2012:《流動人口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和身份認同問題研究》[J]. 《社會學研究》,第 5 期。
[2] 龔鋒、李智、雷欣,2017:《努力對機會不平等的影響:測度與比較》[J]. 《經濟研究》,第 3 期。
[3] 郭繼強、姜儷、陸利麗,2011:《工資差異分解方法述評》[J]. 《經濟學(季刊)》,第 2 期。
[4] 馬超、宋澤、顧海,2016:《醫保統籌對醫療服務公平利用的政策效果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第 1 期。
[5] 馬超、顧海、宋澤,2017:《補償原則下的城鄉醫療服務利用機會不平等》[J]. 《經濟學(季刊)》,第 4 期。
[6] 馬超、曲兆鵬、宋澤,2018:《城鄉醫保統籌背景下流動人口醫療保健的機會不平等——事前補償原則與事后補償原則的悖論》[J]. 《中國工業經濟》,第 2 期。
[7] 牛建林,2013:《人口流動對中國城鄉居民健康差異的影響》[J]. 《中國社會科學》,第 2 期。
[8] 秦立建、王震、蔣中一,2014:《農民工的遷移與健康——基于遷移地點的 Panel 證據》[J]. 《世界經濟文匯》,第 6 期。
作者:馬超 曲兆鵬*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