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xué)中實(shí)在謂詞難題的解決
時(shí)間:2019年12月18日 分類(lèi):文學(xué)論文 次數(shù):
【摘要】在康德哲學(xué)中,實(shí)在謂詞難題由以下命題構(gòu)成:1.存在等于實(shí)存;2.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3.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4.存在不是實(shí)在謂詞;5.所以,存在既是實(shí)在謂詞,又不是實(shí)在謂詞。為了化解這種矛盾,目前學(xué)界有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否定命題1,認(rèn)為存在不同于實(shí)存;另一種是否定命題3,認(rèn)為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然而,它們都難以成立,因?yàn)榇嬖诤蛯?shí)存在充當(dāng)謂詞時(shí)是一回事,實(shí)在謂詞是綜合命題的謂詞。本文同樣否定命題3,但通過(guò)區(qū)分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來(lái)解決。實(shí)在謂詞是客觀綜合命題的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是主觀綜合命題的謂詞,因而并非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都是實(shí)在謂詞。存在不是實(shí)在謂詞,而是現(xiàn)實(shí)謂詞。
【關(guān)鍵詞】存在;實(shí)存;實(shí)在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主觀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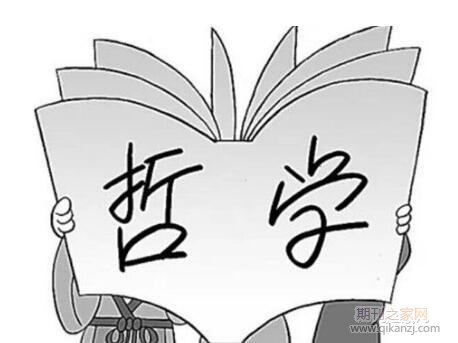
“存在問(wèn)題”很重要,它“涉及到我們?nèi)祟?lèi)的整個(gè)看待世界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 ”王慶節(jié):《海德格爾、存在問(wèn)題與創(chuàng)新性思維(上)》,《廣西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第1期,第49頁(yè)。 。2019年1月,在“康德哲學(xué)愛(ài)好者共同體”微信群,筆者和幾位學(xué)界同仁就康德對(duì)“存在問(wèn)題”的論述展開(kāi)激烈爭(zhēng)論。這場(chǎng)爭(zhēng)論涉及康德如何批判本體論證明、邏輯謂詞和實(shí)在謂詞有什么區(qū)別等論題。從中,筆者發(fā)現(xiàn)了實(shí)在謂詞難題。
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從不同側(cè)面觸及到這一難題,比如黑格爾、海德格爾、伍德(Allen Wood)認(rèn)為存在(Sein)等于實(shí)存(Existenz)本文采用鄧曉芒先生的譯名,統(tǒng)一將Sein譯為存在,Dasein譯為存有,Existenz譯為實(shí)存。 ,楊云飛持相反立場(chǎng),泰斯(Robert Theis)和隆古尼斯(Beatrice Longuenesse)提出實(shí)在性表示事物的可能性,舒遠(yuǎn)招主張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但是,目前還沒(méi)有人將實(shí)在謂詞難題明確提出來(lái)。本文第一部分就是闡明這一難題。接著,將復(fù)述學(xué)界已有的兩種解決方案,對(duì)其進(jìn)行反駁,雖然他們未必意識(shí)到自己的貢獻(xiàn)。在此基礎(chǔ)上,筆者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最后回應(yīng)兩種合理的質(zhì)疑。
一、實(shí)在謂詞難題
實(shí)在謂詞難題是有關(guān)實(shí)在謂詞的矛盾現(xiàn)象。一方面,眾所周知,“存在顯然不是一個(gè)實(shí)在謂詞”(KrV,A598/B626)《純粹理性批判》引文出自《哲學(xué)叢書(shū)》第37a卷(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 Vernunft. Hrsg. Von Raymund Schmidt. Hamburg :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56.)以下頁(yè)中注將《純粹理性批判》縮寫(xiě)為KrV,并標(biāo)明A、B兩版頁(yè)碼。 ,另一方面,存在似乎又是實(shí)在謂詞,如此陷入矛盾。
存在看上去是實(shí)在謂詞。首先,存在等于實(shí)存,這是學(xué)界的基本共識(shí)。黑格爾明確說(shuō):“實(shí)存或存在——這在此處是同義語(yǔ)。”[德]黑格爾:《邏輯學(xué)》,楊一之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6年,第75頁(yè)。 海德格爾說(shuō):“實(shí)存、存有(Dasein)、亦即存在……”[德]海德格爾:《路標(biāo)》,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1年,第529頁(yè)。 伍德說(shuō):“如果‘存在’或‘實(shí)存’是這類(lèi)實(shí)在謂詞……”Wood. Allen, Kant?s Rational Theolo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06. 他們將存在和實(shí)存交替使用。其次,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正如每個(gè)有理性者都必須明智地承認(rèn)的那樣——任何一個(gè)實(shí)存性命題都是綜合的。”(KrV,A598/B626)既然所有實(shí)存性命題都是綜合的,亦即所有包含實(shí)存謂詞的命題都是綜合的,那么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再次,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某物的規(guī)定[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譯,第109頁(yè)。 ,而“一物的規(guī)定”是實(shí)在謂詞(KrV,A598/B626),因而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既然存在等于實(shí)存,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而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那么不難得出,存在是實(shí)在謂詞。
因此,以下命題構(gòu)成實(shí)在謂詞難題:1.存在等于實(shí)存;2.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3.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4.存在不是實(shí)在謂詞;5.所以,存在既是實(shí)在謂詞,又不是實(shí)在謂詞。為了避免這種矛盾,研究者們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否定命題1,認(rèn)為存在不同于實(shí)存,代表人物是楊云飛;另一種是否定命題3,認(rèn)為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代表人物是舒遠(yuǎn)招舒遠(yuǎn)招教授尚未發(fā)表相關(guān)論文,我把他當(dāng)作第二種解決方案的代表人物是跟他深入交流的結(jié)果。以下對(duì)他的觀點(diǎn)和理由的復(fù)述均跟他本人確認(rèn)過(guò)。 。
二、對(duì)楊云飛的反駁:存在和實(shí)存在充當(dāng)謂詞時(shí)是一回事
楊云飛認(rèn)為存在和實(shí)存(或存有)不同楊云飛認(rèn)為存在和實(shí)存不同,但認(rèn)可實(shí)存和存有是一回事。因此,下文不再區(qū)分實(shí)存和存有。 ,因?yàn)榇嬖谑沁壿嬛^詞,實(shí)存是實(shí)在謂詞;前者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后者是綜合命題的謂詞。在他看來(lái),邏輯謂詞和實(shí)在謂詞的劃分同分析和綜合的區(qū)分是相應(yīng)的楊云飛:《康德對(duì)上帝存有本體論證明的批判及其體系意義》,《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4期,第33—34頁(yè)。 。接下來(lái),筆者先重構(gòu)他的論證,對(duì)其進(jìn)行反駁,然后給出存在等同于實(shí)存的文本依據(jù)。需要申明的是,筆者承認(rèn)存在和實(shí)存語(yǔ)法上的區(qū)別,前者可以做系詞,后者不行參見(jiàn)李科政:《康德的實(shí)存問(wèn)題與本體論批判》,《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4期,第122頁(yè)。 ,只是認(rèn)為它們?cè)诔洚?dāng)謂詞時(shí)是一樣的。
首先,楊云飛認(rèn)為存在是分析命題的謂詞,理由有二:其一,存在是邏輯謂詞,而邏輯謂詞表達(dá)概念的同一性,因而它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其二,由于存在不給主詞概念添加更多東西,因而它是分析命題的謂詞。“通過(guò)‘是’,我們只是把主詞連同它的一切謂詞,也就是把對(duì)象設(shè)定在與我的概念的關(guān)系中,卻沒(méi)有給概念添加更多的東西。”楊云飛:《康德對(duì)上帝存有本體論證明的批判及其體系意義》,《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4期,第33頁(yè)。
然而,這兩個(gè)理由都不能成立。其一,邏輯謂詞和分析命題不具有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毋寧說(shuō),不管是分析還是綜合命題,它們的謂詞都可以是邏輯謂詞。康德說(shuō):“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東西當(dāng)作邏輯謂詞。”(KrV,A598/B626)既然任何東西都可以充當(dāng)邏輯謂詞,那么綜合命題的謂詞也可以充當(dāng)邏輯謂詞。比如,這個(gè)蘋(píng)果是紅色的,“紅色的”就是邏輯謂詞。所以,邏輯謂詞跟命題類(lèi)型無(wú)關(guān)。其二,不僅是存在,實(shí)存也不給主詞概念添加更多東西。這一點(diǎn)楊云飛也承認(rèn),他說(shuō)“現(xiàn)實(shí)的100元錢(qián)與可能的100元錢(qián),就100元錢(qián)這個(gè)概念的分析性的內(nèi)涵而言是相同的”同上。,亦即實(shí)存的100元并沒(méi)有在內(nèi)涵上給100元的概念增加新東西。因此,如果存在因?yàn)闆](méi)有給主詞概念增加新東西而成為分析命題的謂詞,那么基于同樣的理由,實(shí)存也會(huì)是分析命題的謂詞,但他主張實(shí)存是綜合命題的謂詞,這就矛盾了。其實(shí),“沒(méi)有給概念添加更多的東西”只說(shuō)明存在不是客觀綜合命題的謂詞,但它可以是主觀綜合命題的謂詞。關(guān)于客觀綜合和主觀綜合,下文第四部分再詳述。
其次,楊云飛主張實(shí)存是實(shí)在謂詞,因?yàn)閷?shí)存是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而實(shí)在謂詞表示現(xiàn)實(shí)性,所以實(shí)存是實(shí)在謂詞。但是,實(shí)在謂詞僅僅表示事物的可能性,而非現(xiàn)實(shí)性。在此,筆者引用泰斯和隆古尼斯的觀點(diǎn)進(jìn)行說(shuō)明。泰斯認(rèn)為實(shí)在謂詞中的“實(shí)在”是一種“規(guī)定意義上的實(shí)在性,這種實(shí)在性是事物的可能性概念”Theis. Robert, “Kants frühe Theologie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Wolffschen Philosophen”, Die Gottesfrage in der Philosophie Immanuel Kants, Herausgegeben von Norbert Fischer und Maximilian Forschner, Freiburg: Verlag Herder BmbH, 2010, S. 41. 。隆古尼斯則主張可以把一切可能性的理念還原為一切實(shí)在性的理念Longuenesse. Beatrice, “Transcendental Ideal and the Unity of the Critical System”, in Robinso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nt Congress, 1995, p. 526. 。
實(shí)際上,存在和實(shí)存被康德交替使用,它們充當(dāng)謂詞時(shí)的含義是相同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說(shuō):“如果我思維一物,不管我通過(guò)什么謂詞和通過(guò)多少謂詞(哪怕在完全的規(guī)定中)來(lái)思維它,那么就憑我再加上‘該物存在’,也并未對(duì)該物有絲毫的增加。因?yàn)榉駝t的話,所實(shí)存的就并不恰好是該物。”(KrV,A600/B628)他先講在某物的概念上加上“該物存在”,不會(huì)對(duì)該物有絲毫增加;否則的話,所存在的就不是該物了。這個(gè)意思是連貫的。可他寫(xiě)下的卻是:“因?yàn)榉駝t的話,所實(shí)存的就并不恰好是該物。”這說(shuō)明他在交替使用存在和實(shí)存。
不僅如此,存在和實(shí)存被交替使用的現(xiàn)象還出現(xiàn)在《證明上帝存有惟一可能的證據(jù)》(下文簡(jiǎn)稱(chēng)為《證據(jù)》)和《哲學(xué)宗教學(xué)說(shuō)講義》中。文本1:“至于上帝是否是存在,也就是說(shuō),是否被絕對(duì)地設(shè)定,是否實(shí)存,則根本不包括在內(nèi)。”[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80頁(yè)。 文本2:“一切都取決于某物的實(shí)存(Existenz)事實(shí)上是不是該物的一種實(shí)在性,但憑此——某物存在(ist)——沒(méi)有使該物本身變得更完美;它由此并沒(méi)有包含新的謂詞。”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btheilung IV: Vorlesungen. Bd.28/2/2: Vorlesungen über Metaphysik und Rationaltheologie, 2.H?lfte, Teilbd.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2, S. 1027.文本1存在和實(shí)存顯然可以互換,文本2主干部分意思是即使某物的實(shí)存是一種實(shí)在性,它也不能使該物增加新謂詞,插入語(yǔ)“某物存在”對(duì)應(yīng)上一句的某物的實(shí)存,兩處的“實(shí)存”和“存在”可以互換。因此,在康德那里,存在和實(shí)存在充當(dāng)謂詞時(shí)是一回事,因?yàn)樗鼈兌急硎臼挛锏默F(xiàn)實(shí)性,并且在各個(gè)文本中交替使用。所以,試圖區(qū)分存在和實(shí)存的第一種解決方案行不通。
三、對(duì)舒遠(yuǎn)招的反駁:實(shí)在謂詞是綜合命題的謂詞
舒遠(yuǎn)招主張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實(shí)在謂詞要么是分析命題的謂詞,要么是綜合命題的謂詞,既然它是前者,那么實(shí)在謂詞就不是綜合命題的謂詞,亦即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都不是實(shí)在謂詞。因此,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和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都不是實(shí)在謂詞,這兩個(gè)命題在邏輯上是等值的。這一觀點(diǎn)旨在否定實(shí)在謂詞難題的命題3,即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
舒遠(yuǎn)招提供的文本依據(jù)是:“‘存在’顯然不是一個(gè)實(shí)在的謂詞,即不是有關(guān)可以加在一物概念之上的某種東西的一個(gè)概念。”(KrV,A598/B626)他認(rèn)為“可以加在一物概念之上的某種東西的一個(gè)概念”表明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因?yàn)?ldquo;添加”分兩種,一種是在主詞概念之上添加實(shí)存概念,另一種是在其上添加實(shí)在謂詞。由于添加實(shí)存概念是綜合性添加,又由于實(shí)存概念不同于實(shí)在謂詞,因此添加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性的。
誠(chéng)然,在主詞概念上添加實(shí)存概念和添加實(shí)在謂詞不同,但這種不同僅僅是綜合內(nèi)部的,前者的添加是主觀綜合,后者的添加是客觀綜合。它們都跟分析不同。在康德的常見(jiàn)用法中,當(dāng)他要表達(dá)分析的意思時(shí),通常用“包含在……之中”(將enthalten跟in搭配),而當(dāng)他把諸如hinzukommen、hinzufügen等表“添加”的詞跟介詞zu搭配時(shí),往往表示綜合的意思。舒遠(yuǎn)招所引文本的同一段就有明證:“對(duì)象在現(xiàn)實(shí)性方面并不只是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是綜合地添加在我的概念之上。”(KrV,A599/B627)在其他文本中,“添加”也表示綜合的意思。例如,“由于我回顧我從中抽象出這個(gè)物體概念來(lái)的那個(gè)經(jīng)驗(yàn),于是我就……把重量作為謂詞綜合地添加在這概念上”(KrV,A7/B12)。如果康德要表達(dá)分析的含義,他會(huì)說(shuō)實(shí)在謂詞是可以包含在一個(gè)概念之中的某個(gè)東西的概念,但他實(shí)際上說(shuō)的是實(shí)在謂詞添加在一個(gè)概念之上的某個(gè)東西的概念,所以實(shí)在謂詞不是分析命題的謂詞。
另外,舒遠(yuǎn)招的觀點(diǎn)會(huì)造成文本上的兩處割裂。第一處割裂出現(xiàn)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上帝存有之本體論證明的不可能性”第九段如下:
如果我不是發(fā)現(xiàn)了混淆邏輯的謂詞和實(shí)在的謂詞(即一物的規(guī)定)的這種幻覺(jué)幾乎是拒絕一切教導(dǎo)的話,那我就會(huì)希望直截了當(dāng)?shù)赝ㄟ^(guò)對(duì)實(shí)存概念的精確規(guī)定來(lái)打破這一挖空心思的論證了。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東西用作邏輯的謂詞,甚至主詞也可以被自己所謂述;因?yàn)檫壿嫵榈袅艘磺袃?nèi)容。但規(guī)定卻是一個(gè)添加在主詞概念之上的謂詞,它擴(kuò)大了這個(gè)概念。所以它必須不是已經(jīng)包含在這個(gè)概念之中的。(KrV,A598/B626)
舒遠(yuǎn)招認(rèn)為,由于實(shí)在謂詞是一物的規(guī)定,而一物的規(guī)定并不對(duì)應(yīng)最后兩句的“規(guī)定”,因而實(shí)在謂詞不是綜合命題的謂詞。在他看來(lái),最后兩句的“規(guī)定”對(duì)應(yīng)的是第一句中的“實(shí)存概念的精確規(guī)定”,因?yàn)閮商幍?ldquo;規(guī)定”都出現(xiàn)在正文中。他主張本段從第二句到最后,都在論述邏輯謂詞。
他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這一段第一句中的“挖空心思的論證”指本體論證明。它的意思是,正是因?yàn)槲野l(fā)現(xiàn)了混淆兩種謂詞會(huì)拒絕教導(dǎo),所以我不會(huì)直截了當(dāng)?shù)赝ㄟ^(guò)實(shí)存概念的精確規(guī)定反駁本體論證明。這里包含兩個(gè)步驟,第一步是區(qū)分邏輯謂詞和實(shí)在謂詞,第二步通過(guò)實(shí)在謂詞和實(shí)存概念的對(duì)比得出實(shí)存概念的精確規(guī)定。本段完成第一步,后面的段落完成第二步。本段有四句話。第一句交代區(qū)分兩種謂詞的任務(wù),第二句講邏輯謂詞的含義,第三句到本段末尾講實(shí)在謂詞的含義。由于實(shí)在謂詞是一物的規(guī)定,而規(guī)定擴(kuò)大了主詞概念,不包含在主詞概念之中,因而它是綜合命題的謂詞。所以,舒遠(yuǎn)招割裂了本段“一物的規(guī)定”和最后兩句的“規(guī)定”的關(guān)聯(lián)。
第二處割裂出現(xiàn)在《純粹理性批判》和《邏輯學(xué)講義》之間。《邏輯學(xué)講義》說(shuō):“前者包含著規(guī)定,后者僅僅包含邏輯謂詞。”[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譯,第109頁(yè)。 其中“后者”是分析命題。分析命題僅僅包含邏輯謂詞,不包含實(shí)在謂詞,因而實(shí)在謂詞不是分析命題的謂詞。如果如舒遠(yuǎn)招所言,實(shí)在謂詞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是分析命題的謂詞,那么就跟《邏輯學(xué)講義》中的論述不一致。
由此可知,舒遠(yuǎn)招主張的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不符合康德對(duì)“添加”的常見(jiàn)用法,割裂了《純粹理性批判》內(nèi)部?jī)商?ldquo;規(guī)定”的關(guān)聯(lián),還割裂了《純粹理性批判》和《邏輯學(xué)講義》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舒遠(yuǎn)招對(duì)實(shí)在謂詞難題命題3的否定難以成立,實(shí)在謂詞是綜合命題的謂詞。
四、本文的解決方案:存在是現(xiàn)實(shí)謂詞
同樣是否定命題3,即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不過(guò)與舒遠(yuǎn)招不同,筆者主張并非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實(shí)在謂詞,換言之,有些綜合命題的謂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而是現(xiàn)實(shí)謂詞。
現(xiàn)實(shí)謂詞不是康德本人使用的術(shù)語(yǔ),但他的文本蘊(yùn)含了這層含義。康德說(shuō)存在是“對(duì)一物或某些規(guī)定性本身的肯定”(KrV,A598/B626),筆者把對(duì)事物(或?qū)ο?進(jìn)行肯定的謂詞命名為現(xiàn)實(shí)謂詞。這樣一來(lái),謂詞可以分為三類(lèi):邏輯謂詞、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邏輯謂詞是跟主詞不矛盾的謂詞,實(shí)在謂詞是在主詞和謂詞的關(guān)系中擴(kuò)大主詞概念的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則是主體在主詞概念和它的對(duì)象的關(guān)系中、將對(duì)象肯定下來(lái)的謂詞。
從邏輯謂詞、實(shí)在謂詞到現(xiàn)實(shí)謂詞,它們是層層遞進(jìn)的關(guān)系。邏輯謂詞是表示邏輯可能性的謂詞,它僅僅要求謂詞跟主詞在邏輯上不矛盾雖然康德說(shuō)“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東西用作邏輯謂詞”(KrV,A598/B626),但跟主詞矛盾的詞不可以充當(dāng)邏輯謂詞。邏輯謂詞對(duì)應(yīng)“先驗(yàn)的理想”中的“可規(guī)定性原理”,這條原理是基于矛盾律的。所以,邏輯謂詞是邏輯可能的謂詞,不能跟主詞矛盾。 。實(shí)在謂詞是表示事物的可能性的謂詞,它除了要求跟主詞不矛盾,還要求主詞符合知性原理或理性原理。現(xiàn)實(shí)謂詞是表示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的謂詞,它不僅要求謂詞跟主詞不矛盾,主詞符合知性原理或理性原理,還要求為主詞提供質(zhì)料(知覺(jué))。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謂詞謂述的主詞而言,“為這概念提供素材的知覺(jué),是現(xiàn)實(shí)性的唯一品格”(KrV,A225/B273)。因此,邏輯謂詞、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對(duì)應(yīng)邏輯的可能性、事物的可能性和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這三個(gè)層次之間的要求依次增強(qiáng)。
由于實(shí)在謂詞難題涉及對(duì)象的內(nèi)容,而邏輯謂詞抽掉了一切內(nèi)容,因而重要的不是區(qū)分邏輯謂詞和實(shí)在謂詞,而是區(qū)分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對(duì)于所有S是P句型的命題而言,實(shí)在謂詞關(guān)注的是S和P的關(guān)系,例如“這個(gè)蘋(píng)果是紅色的”,“紅色的”作為實(shí)在謂詞,它述說(shuō)的是這個(gè)蘋(píng)果具有紅色的屬性。但對(duì)于“某物存在”的命題而言,“存在”作為現(xiàn)實(shí)謂詞,不再述說(shuō)“某物”和“存在”的關(guān)系,而是關(guān)注該物的概念和該物的關(guān)系。例如“這個(gè)蘋(píng)果存在”,它不是說(shuō)這個(gè)蘋(píng)果有一種被稱(chēng)為“存在”的屬性,而是說(shuō)主體通過(guò)“存在”這一謂詞,超出蘋(píng)果的概念,將蘋(píng)果這一對(duì)象斷定為現(xiàn)實(shí)存在。
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有四大差異。第一,實(shí)在謂詞涉及主詞和謂詞的關(guān)系,而現(xiàn)實(shí)謂詞涉及主體的主詞概念和它的對(duì)象的關(guān)系。“在一切判斷中,從其中主詞對(duì)謂詞的關(guān)系來(lái)考慮……要么是謂詞B屬于主詞A,是(隱蔽地)包含在A這個(gè)概念中的東西;要么是B完全外在于概念A(yù),雖然它與概念A(yù)有連結(jié)。在前一種情況下我把這判斷叫做分析的,在第二種情況下則稱(chēng)為綜合的。”(KrV,A7/B11)實(shí)在謂詞作為綜合命題的謂詞,是從主詞對(duì)謂詞的關(guān)系來(lái)考慮的。然而,對(duì)于“存在”這類(lèi)現(xiàn)實(shí)謂詞來(lái)說(shuō),我們?cè)谀澄镏蠹由?ldquo;某物存在”,它不涉及主詞和謂詞的關(guān)系,而是肯定了主詞和主詞對(duì)象之間的關(guān)系。例如,“上帝存在”,“我對(duì)于上帝的概念沒(méi)有設(shè)定什么新的謂詞,而只是把……對(duì)象設(shè)定在與我的概念的關(guān)系中”(KrV,A599/B627)。通過(guò)用“存在”謂述上帝,我將上帝的對(duì)象設(shè)定在與我的上帝概念的關(guān)系中,確切地說(shuō),我將上帝概念指稱(chēng)的對(duì)象肯定下來(lái)了。
第二,實(shí)在謂詞不肯定主詞對(duì)象的存有狀態(tài),現(xiàn)實(shí)謂詞對(duì)其存有狀態(tài)進(jìn)行肯定。“所有的謂詞與其主體的關(guān)系都絕不表明某種實(shí)存的東西,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已經(jīng)被假定為實(shí)存的。”[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81頁(yè)。黑體是筆者所加。 實(shí)在謂詞只是假定主詞對(duì)象是實(shí)存的,現(xiàn)實(shí)謂詞卻將主詞對(duì)象的存有狀態(tài)肯定下來(lái)。二者的差異可以用如下兩個(gè)命題來(lái)刻畫(huà):實(shí)在謂詞表明,假如有主詞對(duì)象,那么主詞概念和謂詞有如此這般的關(guān)系;而現(xiàn)實(shí)謂詞表明,真的有連同其一切謂詞的主詞對(duì)象。
第三,實(shí)在謂詞表示事物的可能性,現(xiàn)實(shí)謂詞表示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Wirklichkeit)。實(shí)在謂詞是關(guān)于事物的實(shí)在性(Realit?t)的謂詞。實(shí)在性盡管是質(zhì)的范疇,卻跟模態(tài)范疇有密切關(guān)系;但它不表示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而表示事物的可能性。實(shí)在性是對(duì)事物的先驗(yàn)的肯定,它是“與感覺(jué)相應(yīng)的東西”即“先驗(yàn)質(zhì)料”(KrV,A143/B182)。但與感覺(jué)相應(yīng)的東西不同于感覺(jué),而只是指向感覺(jué)。先驗(yàn)質(zhì)料也不同于經(jīng)驗(yàn)質(zhì)料,前者跟事物的可能性相關(guān),后者則跟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相關(guān)。“那種構(gòu)成質(zhì)料的東西(與感覺(jué)相應(yīng)的東西),即在現(xiàn)象中的實(shí)在性,卻必須被給予出來(lái),舍此這種關(guān)系甚至根本不能被思維,因而它的可能性也就不能被表現(xiàn)出來(lái)了。”(KrV,A581/B609)“構(gòu)成質(zhì)料的東西”指現(xiàn)象中的實(shí)在性,即先驗(yàn)質(zhì)料。如果先驗(yàn)質(zhì)料沒(méi)有被給予,那么感官對(duì)象和主體思維的關(guān)系的可能性不能被表現(xiàn)出來(lái),也就是說(shuō),感官對(duì)象不能被主體肯定為可能存有。這表明先驗(yàn)質(zhì)料跟感官對(duì)象的可能存有相關(guān),亦即實(shí)在性跟事物的可能性相關(guān)。
在“先驗(yàn)的理想”一節(jié),實(shí)在性表示事物的可能性這一觀點(diǎn)得到明確的文本支持。例證1:按照通盤(pán)規(guī)定性原理,每一物的特殊可能性以全部可能性為根據(jù),“由于它(通盤(pán)規(guī)定性原理)把全部可能性預(yù)設(shè)為先天的條件,所以它把每一物表現(xiàn)得如同從其在那個(gè)全部可能性中所擁有的份額里推導(dǎo)出自己特有的可能性一樣”(KrV,A572/B600)。在另一處,康德說(shuō):“一切物的可能性將會(huì)以作為某種根據(jù)而不是作為總和的最高實(shí)在性為基礎(chǔ)。”(KrV,A579/B607)很明顯,最高實(shí)在性被當(dāng)作全部可能性來(lái)看待。
例證2:在“先驗(yàn)的理想”第四段,康德講到一切可能性的總和的理念的對(duì)象化。“雖然關(guān)于一切可能性的總和的這個(gè)理念,就這總和作為條件而成為對(duì)每一物進(jìn)行通盤(pán)規(guī)定的基礎(chǔ)而言,在可能構(gòu)成這個(gè)總和的那些謂詞上本身還是未規(guī)定的……但在進(jìn)一步的研究中我們卻發(fā)現(xiàn),這個(gè)理念……成了有關(guān)一個(gè)單獨(dú)對(duì)象的概念。”(KrV,A573/B601)而在同一節(jié)的第十八段,康德又講“關(guān)于一切實(shí)在性的總和的這個(gè)理念的實(shí)體化”(KrV,A582/B610),即把這個(gè)理念看作一個(gè)單獨(dú)對(duì)象。這兩處文本表明,實(shí)在性和可能性的表述在交替使用。
例證3:“諸物的一切可能性……就被看作是派生的了,而惟一只有那個(gè)把一切實(shí)在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物之可能性才被看作是本源的。”(KrV,A578/B606)按理說(shuō),本源的物的可能性是把諸物的一切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但寫(xiě)下的卻是把一切實(shí)在性包含在自身之中,這說(shuō)明康德將實(shí)在性和可能性交替使用。
上述三個(gè)例證表明,實(shí)在性表示事物的可能性,而現(xiàn)實(shí)謂詞表示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表示現(xiàn)實(shí)性的是對(duì)對(duì)象的肯定,例如一百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塔勒“意味著對(duì)象及其肯定本身”(KrV,A599/B627)。 可能性和現(xiàn)實(shí)性的差別在于,前者只是頭腦中的觀念,后者既是頭腦中的觀念,又是現(xiàn)實(shí)存在的對(duì)象。“一百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塔勒所包含的絲毫也不比一百個(gè)可能的塔勒更多……但是在我的財(cái)產(chǎn)狀況中,現(xiàn)實(shí)的一百塔勒比一百塔勒的單純概念(即一百塔勒的可能性)有更多的東西。”(KrV,A599/B627)在什么意義上現(xiàn)實(shí)的東西不比單純可能的東西更多,又在什么意義上前者比后者多一點(diǎn)?這個(gè)問(wèn)題在《證據(jù)》中得到明確回答。“在一個(gè)實(shí)存的東西中比在一個(gè)單純可能的東西中沒(méi)有設(shè)定任何更多的東西(因?yàn)樵谶@種情況下說(shuō)的是該事物的謂詞);然而,借助某種實(shí)存著的東西要比借助一個(gè)單純可能的東西設(shè)定了更多的東西,因?yàn)檫@也涉及對(duì)事物自身的絕對(duì)肯定。”[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82頁(yè)。 現(xiàn)實(shí)的東西跟單純可能的東西謂詞一樣多,但它多出對(duì)對(duì)象的絕對(duì)肯定。黑格爾對(duì)此有深刻的洞見(jiàn):“如果我占有了一百元錢(qián),則我便實(shí)際占有一百元錢(qián),并且同時(shí)也具有一百元錢(qián)的觀念。”[德]黑格爾:《哲學(xué)史講演錄》第4卷,賀麟、王太慶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78年,第315頁(yè)。
第四,實(shí)在謂詞是客觀綜合命題的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是主觀綜合命題的謂詞。客觀綜合就主詞和謂詞的關(guān)系而言,它要求擴(kuò)大主詞概念;主觀綜合不擴(kuò)大主詞概念,卻仍然是種綜合。“模態(tài)的諸原理并不是客觀綜合的,因?yàn)榭赡苄浴F(xiàn)實(shí)性和必然性這些謂詞絲毫也不因?yàn)樗鼈儗?duì)于對(duì)象的表象還有所補(bǔ)充就擴(kuò)大它們所說(shuō)的那個(gè)概念。但由于它們畢竟總還是綜合性的,所以它們就只是主觀綜合的,就是說(shuō),它們對(duì)一物(實(shí)在之物)的概念……增添了這概念在其中產(chǎn)生并有自己的位置的那種認(rèn)識(shí)能力。”(KrV,A234/B286)現(xiàn)實(shí)性范疇不擴(kuò)大主詞概念,因而當(dāng)它添加到主詞之上時(shí),只是一種主觀綜合。主觀綜合要求增添主詞概念由以產(chǎn)生的認(rèn)識(shí)能力,亦即主觀綜合表現(xiàn)在主體超出主詞概念,將它的對(duì)象的存有狀態(tài)斷定下來(lái)。這也是一種綜合,但不是就客體本身的規(guī)定而言,而是就客體與主體的認(rèn)識(shí)能力的關(guān)系而言的。當(dāng)我們將可能性這一范疇添加到某物的概念,得到“某物是可能的”時(shí),我們就將該物的存有狀態(tài)斷定為可能的。同理,當(dāng)我們將現(xiàn)實(shí)性和必然性范疇添加到主詞,得到“某物是現(xiàn)實(shí)的”或“某物是必然的”時(shí),我們將該物的存有狀態(tài)斷定為現(xiàn)實(shí)的或必然的。客觀綜合和主觀綜合之所以是綜合,是因?yàn)樗鼈兌汲隽酥髟~概念;前者的超出表現(xiàn)在擴(kuò)展主詞的含義,后者的超出則是在主詞概念之外,將這個(gè)概念指稱(chēng)的對(duì)象肯定下來(lái);前者從單純的概念層面來(lái)看,后者則是從主體的概念和對(duì)象的關(guān)系來(lái)看的。
因此,實(shí)在謂詞就主詞和謂詞的關(guān)系而言擴(kuò)大了主詞概念,是客觀綜合命題的謂詞;而現(xiàn)實(shí)謂詞雖然不給主詞概念增加新謂詞,卻超出這個(gè)概念,將它的對(duì)象肯定下來(lái),它是主觀綜合命題的謂詞。這說(shuō)明有些綜合命題的謂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因此,所有綜合命題的謂詞都是實(shí)在謂詞的觀點(diǎn)是不能成立的,實(shí)在謂詞難題得以解決。這樣一來(lái),我們也清楚了,存在不是實(shí)在謂詞,而是現(xiàn)實(shí)謂詞。
五、回應(yīng)合理的質(zhì)疑
以上解決方案可能面臨兩個(gè)重要質(zhì)疑,一是針對(duì)實(shí)在謂詞的,二是來(lái)自《證據(jù)》的。由本文第三和第四部分可知,實(shí)在謂詞既是綜合命題的謂詞,又是關(guān)于事物的實(shí)在性的謂詞,可這兩個(gè)觀點(diǎn)似乎不一致。這集中表現(xiàn)在如下問(wèn)題:分析命題的謂詞能夠成為實(shí)在謂詞嗎?這類(lèi)謂詞不是綜合命題的謂詞,但它們不表示事物的實(shí)在性嗎?接下來(lái),筆者以“上帝是全能的”這個(gè)分析命題為例,討論“全能的”是不是實(shí)在謂詞。
在筆者看來(lái),“全能的”在這個(gè)命題中不是實(shí)在謂詞。但很多人持相反的立場(chǎng),他們主張“全能的”是實(shí)在謂詞。文本依據(jù)如下:
“Sein”顯然不是一個(gè)實(shí)在的謂詞,即不是有關(guān)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種東西的一個(gè)概念。它只不過(guò)是對(duì)一物或某些規(guī)定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邏輯上,它只是一個(gè)判斷的系詞。“上帝是全能的”這個(gè)命題包含有兩個(gè)概念,它們擁有自己的對(duì)象“上帝”和“全能”;小詞“是”并非又是一個(gè)另外的謂詞,而只是把謂詞設(shè)定在與主詞的關(guān)系中的東西。(KrV,A598/B626)
他們認(rèn)為引文中“上帝是全能的”這個(gè)例子是為了比較系詞“是”和謂詞“全能的”的差異。由于“是”不同于“全能的”,又由于“是”不是實(shí)在謂詞,因而“全能的”是實(shí)在謂詞。但是,他們的理解忽視了整段話的語(yǔ)境。這段話的中心句是第一句,即“Sein”不是實(shí)在謂詞。它為什么不是實(shí)在謂詞?理由有二:其一,當(dāng)“Sein”作為對(duì)規(guī)定性的肯定時(shí),它只是系詞,系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其二,當(dāng)“Sein”作為對(duì)對(duì)象的肯定時(shí),它也不是實(shí)在謂詞,而是現(xiàn)實(shí)謂詞。這是整段的邏輯結(jié)構(gòu)。在論述第一個(gè)理由時(shí),康德以“上帝是全能的”為例。這個(gè)例子不是為了比較系詞“是”和謂詞“全能的”的差異,而是為了表明“是”作為系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換言之,這個(gè)例子中的主詞“上帝”和謂詞“全能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系詞“是”。任何一個(gè)S是P句型的命題,不管S和P指代什么,都可以達(dá)到康德要論證的目的,因?yàn)檫@個(gè)句型的命題有系詞“是”。系詞連謂詞都不是,自然不會(huì)是實(shí)在謂詞。因此,這段話得不出“全能的”是實(shí)在謂詞的結(jié)論。
在“上帝是全能的”這個(gè)分析命題中,“全能的”不是實(shí)在謂詞。實(shí)在謂詞必須擴(kuò)大主詞概念,不包含在主詞概念之中,而分析命題的謂詞僅僅表示概念的同一性,包含在主詞概念之中,因此,一切分析命題的謂詞都不是實(shí)在謂詞。進(jìn)一步看,分析命題的謂詞也不表示事物的實(shí)在性。因?yàn)閷?shí)在性是質(zhì)的范疇,當(dāng)它被添加在某物之上時(shí),主謂詞之間構(gòu)成客觀綜合關(guān)系。例如“某物是實(shí)在的”,“實(shí)在的”擴(kuò)展了“某物”的含義。所以,分析命題的謂詞只表示事物的說(shuō)明性屬性,并不是實(shí)在謂詞那樣的擴(kuò)展性屬性。許多人認(rèn)為康德說(shuō)的實(shí)在謂詞是事物的屬性,其實(shí)不準(zhǔn)確。實(shí)在謂詞只是對(duì)事物有所擴(kuò)展的屬性,而不是包含在事物之中的屬性,換言之,它是事物的那部分?jǐn)U展性屬性。這是因?yàn)椋鶕?jù)“上帝存有之本體論證明的不可能性”一節(jié)的第九段,實(shí)在謂詞只能是綜合命題的謂詞。
還有一個(gè)重要質(zhì)疑來(lái)自《證據(jù)》。它發(fā)表于1763年,是前批判時(shí)期的作品。陳艷波提醒說(shuō),“我們必須注意前批判時(shí)期和批判時(shí)期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陳艷波:《康德對(duì)“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批判中的“存在”論題》,《現(xiàn)代哲學(xué)》2009年第4期,第83頁(yè)。 。如果《證據(jù)》和《純粹理性批判》的思想不一致,那么筆者的論證效力將大打折扣。看上去兩個(gè)文本確實(shí)不同,前者說(shuō)“存有(Dasein)根本不是某一個(gè)事物的謂詞或者規(guī)定性”[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78頁(yè)。 ,后者卻承認(rèn)存在是現(xiàn)實(shí)謂詞。于是,問(wèn)題出現(xiàn)了:存在(或存有)能夠充當(dāng)謂詞嗎?
回答是肯定的。首先,《證據(jù)》沒(méi)有否認(rèn)存有是謂詞。最直接的證據(jù)是:“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把存有這一表述當(dāng)作謂詞使用。”同上,第79頁(yè)。 實(shí)際上,它跟《純粹理性批判》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都主張存有不是實(shí)在謂詞。因?yàn)?ldquo;存有根本不是某一個(gè)事物的謂詞或者規(guī)定性” 同上,第78頁(yè)。 ,而一物的規(guī)定性正是實(shí)在謂詞。其次,《純粹理性批判》也有直接證據(jù)表明存有是謂詞。“如果你承認(rèn)……任何一個(gè)實(shí)存命題是綜合的,那么你如何還會(huì)主張實(shí)存謂詞不可以無(wú)矛盾地被取消呢?”(KrV,A598/B626)這句話表明,康德是承認(rèn)實(shí)存可以做謂詞的。
可能有人會(huì)追問(wèn),既然存有是謂詞,當(dāng)它加到主詞上時(shí),為什么不給主詞增加新謂詞?因?yàn)樵谥髟~的可能謂詞之中,有一個(gè)是存有,所以當(dāng)作為現(xiàn)實(shí)謂詞的存有再加上去以后,并沒(méi)有擴(kuò)大原有的謂詞庫(kù)。也就是說(shuō),原來(lái)謂詞庫(kù)里有多少謂詞,現(xiàn)在還是這么多謂詞。但作為可能謂詞的存有和作為現(xiàn)實(shí)謂詞的存有,畢竟是不同的。前者從主謂關(guān)系著眼,它跟紅色這類(lèi)謂詞一樣,是屬于主詞對(duì)象的一種屬性。我們可以從紅花中分析出紅色的屬性,也可以從最高實(shí)在的存在者中分析出存有的屬性。但后者是從主體的主詞概念和它的對(duì)象的關(guān)系著眼,它無(wú)關(guān)乎主詞對(duì)象的屬性,而是主體對(duì)主詞對(duì)象的肯定。一旦肯定下來(lái),主詞對(duì)象就能通過(guò)知覺(jué)在經(jīng)驗(yàn)中被給予出來(lái)。
綜上所述,分析命題的謂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證據(jù)》中盡管說(shuō)到存有不是事物的謂詞,但它的確切含義是存有不是實(shí)在謂詞。所以,盡管上述兩個(gè)質(zhì)疑很尖銳,但筆者的解決方案仍然能夠成立。
上文提到,實(shí)在謂詞難題由五個(gè)命題構(gòu)成。楊云飛的解決方案是否定命題1,主張存在不同于實(shí)存。可是,當(dāng)存在和實(shí)存充當(dāng)謂詞時(shí),它們都表示事物的現(xiàn)實(shí)性,而且被康德交替使用,因而存在和實(shí)存是一回事。舒遠(yuǎn)招的解決方案是否定命題3,主張實(shí)在謂詞是分析命題的謂詞。但文本表明實(shí)在謂詞是綜合命題的謂詞。所以他們的解決方案都行不通。他們都預(yù)設(shè)了謂詞只有兩種:邏輯謂詞和實(shí)在謂詞。
然而,在它們之外,還有許多其他類(lèi)型的謂詞,比如非邏輯謂詞、非實(shí)在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等。因此,如果認(rèn)為一個(gè)謂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就是邏輯謂詞,這種非此即彼的看法是不對(duì)的。同實(shí)在謂詞難題相關(guān)的謂詞有三類(lèi):邏輯謂詞、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重點(diǎn)在于區(qū)分實(shí)在謂詞和現(xiàn)實(shí)謂詞。實(shí)在謂詞是客觀綜合命題的謂詞,現(xiàn)實(shí)謂詞是主觀綜合命題的謂詞,這表明有些綜合命題的謂詞不是實(shí)在謂詞。因此,實(shí)在謂詞難題的命題3不成立,這一難題得以解決。
哲學(xué)方向論文范文:盧梭與作為哲學(xué)問(wèn)題的自戀
【摘要】自戀不僅是一個(gè)精神分析學(xué)的專(zhuān)門(mén)術(shù)語(yǔ),它還關(guān)乎一直潛藏于哲學(xué)史中的主體設(shè)定及其合法性的問(wèn)題。這兩個(gè)方面都集中體現(xiàn)于盧梭的關(guān)于自我、語(yǔ)言和他者的多樣化的文本之中。這既標(biāo)志著贏得一種個(gè)體性的必要重返,也暗示著一種固守其中的危險(xiǎn)。因而,我們需要對(duì)這一概念進(jìn)行轉(zhuǎn)換或限定。在盧梭那里,自戀首先體現(xiàn)為自戀(amour?propre)與自愛(ài)(amourdesoi)的根本區(qū)分。由此,盧梭衍生出一系列的解決方向,但它們并不能被完全還原為心理學(xué)或倫理學(xué)的范疇。
- 哲學(xué)與美學(xué)影響下的當(dāng)代中國(guó)劍舞創(chuàng)作
- 從法統(tǒng)到天道對(duì)《史記·伯夷列傳》的政治哲學(xué)詮釋
- 實(shí)踐音樂(lè)教育哲學(xué)視野下社區(qū)音樂(lè)課程發(fā)展研究
- 文藝思想的正本清源與守正創(chuàng)新
- 從《人性論》談休謨的哲學(xué)研究方法
- 建構(gòu)與批判:國(guó)內(nèi)旅游研究中的哲學(xué)視角反思
- 金岳霖與維特根斯坦:形而上學(xué)批判與未來(lái)哲學(xué)
- 本雅明歷史哲學(xué)維度中的“靈韻”概念*
- 盧梭與作為哲學(xué)問(wèn)題的自戀
SCI期刊目錄
熱門(mén)核心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fù)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fù)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yī)學(xué)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zhuān)業(yè)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qū)和影響
- 2025-02-10經(jīng)管專(zhuān)業(yè)快速發(fā)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jiàn)刊快檢索快的EI會(huì)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huì)議在哪發(fā)論文,解答及指導(dǎo)
- 2025-03-01EI會(huì)議論文值得發(fā)嗎?2025EI會(huì)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shù)據(jù)庫(kù)?scopus數(shù)據(jù)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lèi)期刊
翻譯潤(rùn)色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yīng)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教師能在國(guó)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guó)際中文期刊評(píng)職稱(chēng)承認(rèn)嗎
期刊知識(shí)
- 2025-04-01復(fù)合材料科學(xué)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jí)
- 2025-03-2915本教育類(lèi)雙核心期刊!門(mén)檻低,
發(fā)表指導(dǎo)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jié)能領(lǐng)域論文選題31個(gè),
- 2025-03-28電子技術(shù)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xiàn)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fā)表的論文文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