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理想化中國趣味的文學書寫
時間:2021年10月09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內容摘要:作為日本近現代文學中新思潮派的重要作家,芥川龍之介文學作品題材涉獵廣泛且意趣盎然,因而廣受各國讀者歡迎。 《杜子春》是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題材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其創作靈感源自中國唐代傳奇故事,體現了其濃厚的理想化中國趣味。 而之所以產生這種理想化的中國趣味,主要是因為芥川龍之介從小所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個人獨特的創作理念和大正文壇中國趣味創作偏向的影響。
關鍵詞:芥川龍之介 中國趣味 《杜子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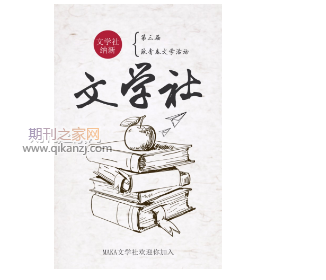
作為日本大正時期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芥川龍之介被譽為日本文壇之“鬼才”,盡管其人生早早畫上了休止符,可是卻留下許多不朽的作品,包括100余篇小說、50余篇小品文、60余篇隨筆等。 “芥川獎”是日本文壇以其名字命名的唯一純文學獎,足以說明芥川龍之介在日本文壇的影響力。 芥川龍之介1920年在《紅鳥》雜志中首次發表《杜子春》,其創作靈感直接源自中國唐代李復言的志怪小說《杜子春傳》,他在借鑒《杜子春傳》的同時又進行了二次創作,描繪出理想的中國形象,展現出別樣的中國趣味。
文學論文范例: 試論文學創作與文學接受的矛盾
一.何為中國趣味
中國趣味一詞在日本最早見于1922年《中國公論》1月號“中國趣味的研究”特集。 根據西原大輔的研究,中國趣味主要包括三類,即“中國人的趣味、日本人的漢學素養與文人教養、對中國事物產生的異國興趣”[1]18-20三類。 大正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大多對中國抱有特別的感情,眾多與中國趣味相關的文學作品由此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中國趣味也就成為該時期日本文學界的“新寵”。 當時的中國趣味類型文學作品大致包括兩種:一是取材于中國古代的作品; 二是取材于20世紀中國近代的(寫實)作品,除小說以外還包括大量的游記。 本文的中國趣味沿用了西原大輔的定義,主要是以芥川龍之介在游歷中國之前的中國古典題材短篇小說《杜子春》中表現出的中國趣味為研究對象。
二.《杜子春》中的中國趣味
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杜子春》雖然繼續沿用了原著的背景和人名,但故事的細節卻有很大的不同。 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杜子春》中的中國趣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地點設定方面:《杜子春》原著的地點設定是在“長安”,但芥川龍之介在改編中將原著中的“長安”改為“洛陽”。 據史料長安是唐朝的正都,洛陽是唐朝的副都,芥川既然沿用故事背景,卻將長安改為洛陽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為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國力強盛的時期,也是文化輸出的鼎盛時期,也是日本崇拜的大國。 在日語中,至今仍用“上洛”來指代去京都(京都即首都)。 芥川龍之介之所以將長安改為洛陽,是因為洛陽在日語中有其特殊意義。 洛陽在日本文化中代表了經濟的繁榮和城市的繁華,日本讀者一讀到洛陽就能聯想到大都城的繁華。 此外,洛陽和中文的“落陽”同音,有“落下的太陽”之意,與文中傍晚的時間點相呼應。
2.情節展開方面:芥川龍之介對原著因地制宜地進行了調整。 首先原著并沒有對故事背景進行交代和描述,但是芥川龍之介卻對此進行了細致詳盡的描述:“彼時洛陽城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可謂是國富民安,街道上門庭若市、川流不息,處處都是祥和富足的場景”[2]58。 他為讀者描繪了唐都的繁榮景象,從社會經濟狀況到優美的自然風光,再到淳樸的中國民風,都一一細致描述出來,為讀者營造出更加濃厚的中國唐朝市井文化氛圍。 關于杜子春成為富人后的奢侈生活的描寫,原著只用“乘肥衣輕,會酒徒,征絲竹歌舞于倡導樓”[3]7十五個字一句帶過,但是芥川龍之介卻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起初過著如同皇帝般的奢靡生活。 佳釀來自蘭陵,桂圓來自桂州,院子中還種植了日易四色的牡丹,圈養了數只白孔雀,偏好各式各樣的寶玉,著錦繡華服,乘坐香車寶馬……”[2]60。 由此可見,芥川龍之介理想中的中國形象是如唐代那樣繁榮富饒的。 其次是有關修煉場所的描寫。 芥川龍之介以峨眉山取代華山云臺峰這一仙居之地。 作為道教名山,華山與道教一樣令人難以捉摸、無法親近; 而作為佛教名山的峨眉山恰恰相反,它令人倍感親近。 再加之華山高峻陡峭,峨眉山則是煙霧繚繞,美不勝收,更似仙境。 華山變成峨眉山,使故事更具縹緲仙境的感覺,同時也符合日本人對于優雅、細致的追求。 此外,由于道教在日本影響力并不大,因此將它更改為日本人熟悉的佛教名地更易讓讀者接受理解。 再者,芥川龍之介在改編中增加了呂洞賓吟誦的內容,仙人攜杜子春御風至峨眉山的路上,吟詠了一首詩:“朝游北海暮蒼梧,袖里青蛇膽氣粗。 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2]66。 原著中沒有這樣的情節,而芥川龍之介卻巧妙地加入呂洞賓的詩,通過增強《杜子春》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來進一步增加中國趣味。 與此同時,他對于修行內容也進行了改編,在描繪杜子春修行情節時將原著“為了兒子放棄修行”改寫為“為了母親放棄修行”。 因為就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而言,“孝”比“慈”更為重要,將原著中杜子春對兒子的愛改寫成對母親的愛,反映了芥川龍之介更為接近中國現實的創作意圖,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時常可以窺見“孝”這一中國傳統思想也就不言自明了。
3.主人公形象設定方面:原著中沒有明示老者的名字而意在為讀者留下一份懸念,但是芥川龍之介在作品中以“鐵冠子”來稱呼老者,并且在他和河西信三的信件中指出:“三國時期左慈的道號就是鐵冠子”[4]278。 芥川龍之介為老者冠以左慈的名號,更加具化了中國仙人的形象,一改老人在原著中樸素的道士形象,通過塑造中國志怪小說中飄逸傳奇的仙人形象,給故事和人物增添了神秘感。
三.芥川龍之介中國趣味的形成原因
芥川龍之介在訪問中國之前,其文學作品中的中國題材作品占據了半壁江山,而這些作品大都給人一種志怪小說所蘊含的虛幻縹緲、神秘莫測的感覺,與其后期創作寫實風格大相徑庭。 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究:
(一)個人所受到的中國古典作品的熏陶
中國與日本互為友鄰,不僅地緣相近,在文化上也存在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聯系,“漢文學在日本古典文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少到平安時代為止,漢文學都是日本文學的正統”[5]7。 芥川龍之介也是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的文人作家之一,他自幼被舅舅撫養長大,而且其舅舅家都是知識分子,因此自幼就有接觸中國古典文學書籍的機會,并在長期的接觸中激發了深層次的求知欲。 芥川龍之介少年時代就已經仔細閱讀過不少中國名著,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著極深的造詣,“《西游記》是我兒時最喜愛的中國名著……我還喜歡讀《水滸傳》,時至今日仍喜歡”[6]234。 此外,芥川龍之介酷愛收藏中國古代典籍,據統計有漢書188種,共計千余冊,甚至包括《太平廣記》、《唐代叢書》、《明詩綜》等大部頭作品,有關古典注釋書的收藏也數量頗豐,這也為其在文學創作中能夠嫻熟運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進行創作提供了堅實的話基礎。 直至親身訪問中國,芥川龍之介此前一直依靠閱讀中國古代典籍來了解中國,并以古代中國為藍圖創造出一個個充滿奇幻和浪漫色彩的烏托邦世界。
(二)個人獨特的創作理念
在《澄江堂雜記》三十一章《古昔》中,芥川龍之介對自己經常創作歷史題材作品的緣由作出解釋,“為了最有力地表現小說的主題,需要不可思議的事件。 像這樣,強調非正常環境尤其重要”[7]200。 因此,故事的時間和地點通常就不能選定在“這里”。 故事距離感的遠近與讀者的接受和感覺直接相關,距離太遠會使得讀者不了解作品故事的背景而不能很好地理解,距離太近又會使讀者缺少神秘感和新鮮感。 由此,芥川龍之介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中國,在明確主題的同時也不會招致讀者的反感,這體現了芥川龍之介“支那物”獨特的創作理念。 這種獨特的創作理念同樣也有機運用在《杜子春》這一作品中,沒落的貴公子、失蹤的仙人、深藏地表之下的黃金、峨眉陡峭險峻的山峰、地獄中不尋常的經歷、奢靡的日常生活、泰山南麓隱藏的世外桃源、起伏豐富的情節和變化的場面使得該作品具有中國志怪小說傳奇般的色彩。 正是基于“支那物”的文學創作理念,使得故事盡管發生年代久遠,也非現實空間中所存在,但合理的空間界定和神秘色彩反而更凸顯這種真實感。 又如芥川龍之介在描寫古代中國名城洛陽時所營造出的繁華喧囂的氛圍和主人公在經歷生活的艱辛后又隱居在世外桃源的心歷路程等,所體現的不僅僅是傳奇故事的完美結局,更是他為讀者描繪的對“心靈城堡”的想象和真誠的向往,由此為讀者帶來閱讀的安心感和真實感。
(三)大正文壇的中國趣味偏向
經過明治時代的“西洋化”,日本在大正時期邁向政治經濟全面繁榮的階段,彼時日本古典文學及傳統漢文學受到歐洲近代文學思潮的壓制。 可是日本的迅猛發展并不能讓日本國民迅速適應這一現實,尤其是受漢文學影響的文人,他們對理想世界的渴望愈加強烈,這一時期的文人作家也被認為是“日本人與自己真正理解的漢文學和中國文化產生了的裂痕之時的最后一代人”[8]13。 一方面,他們的中國浪漫主義詩學傳統根深蒂固,可現實中又不得不接受追求科學、理性的歐洲近代文學思潮的沖擊,所以這部分文人作家認為“概念上的中國”至關重要,“日本人腦海中所構造的中國更像是虛無縹緲的蓬萊仙境,是充滿了浪漫故事、溫柔繾綣、風景、各種奇談的舞臺”[9]36。 盡管“東洋”文明要落后于時代腳步,但是有著“西洋”文明所無法比擬的歷時性與傳奇性。 西方近代文明在大正時期雖然對日本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文壇地位仍是一枝獨秀,畢竟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其浩瀚的文學典籍和傳統文化長久并深層次影響了同處東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 由此,日本文壇在經歷西洋文學創作熱潮后,在大正時代又再次回歸中國古典題材文學創作,形成了大正文壇的中國趣味偏向。 芥川龍之介也被深深攜卷在這一浪潮中并創作了數部以中國古代古典文學為題材的歷史小說。
再者,正如愛德華.W.賽德在其著作《東洋學》中所說:“日本雖然屬于東方,但由于較早被西方化并取得了成果,所以對中國的一部分地區也進行了殖民統治,應該稱之為‘東洋的西洋’”[10]3。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雖雄心勃勃地謀求對外擴張,但從日本特殊的集主客體為一身的存在模式來看,其本質上仍屬東方國家,無法切斷這條千年的歷史紐帶,使其無法成為真正的西方國家。 大正文壇對中國趣味的偏向的原因主要在于日本作家不能跳脫出自身的文化,以真正的西方人的視角看待中國,又因為中國文化對其長期的影響,從而使得大正作家依然充滿著對“幻想中國”的憧憬和想象。
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杜子春》的題材雖是源于中國唐代傳奇故事,但卻不是簡單重復的改編和復刻,而是基于其獨特創作理念的二次創作,忠實反映了芥川龍之介到訪中國之前的文學創作中理想化中國趣味。 這種理想化中國趣味來源于芥川龍之介所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個人獨特的“支那物”創作理念和大正文壇中國趣味創作偏向,《杜子春》可謂是其理想化中國趣味的文學書寫和實踐。 芥川龍之介的這種理想化中國趣味一直延續到其到訪中國之前,是其訪問中國后認清當時中國現實、轉向寫實風格之前文學創作的主流。
參考文獻
[1]西原大輔.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大正日本の中國幻想[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
[2]芥川龍之介.蜘蛛の糸·杜子春[M].東京:新潮社,1968.
[3]李復言.續玄怪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二十卷——河西信三宛昭和二年二月三日[M].東京:巖波書店,1997.
[5]張龍妹、曲莉.日本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二十卷[M].東京:巖波書店,1997.
[7]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五卷[M].東京:巖波書店,1997.
[8]王曉平.梅紅櫻粉一日本作家與中國文化[M].甘肅: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
[9]西原大輔.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大正日本の中國幻想[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
[10]愛德華·W·賽德:東方學.王宇根譯[M].北京:三聯書店,1999.
作者:汪藝 戴詩琳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