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對越中鄉賢詩文集的搜集、閱讀與闡釋
時間:2022年01月21日 分類:文學論文 次數:
【摘要】周作人收藏并閱讀了近三百部越人詩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學立場和“儒家人文主義”的思想視角,他對鄉賢著作的閱讀和闡釋帶有鮮明的個人癖好。他對那些能夠獨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別感興趣,對尊重科學常識、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別關注,對鄉賢詩文中提及的故鄉景物寄托了思鄉之情。但是,周作人對先賢著作的閱讀和接受并非沒有問題,由于思想立場的偏狹,他對陸游、王陽明等人的理解有失片面。
【關鍵詞】周作人;越中鄉賢;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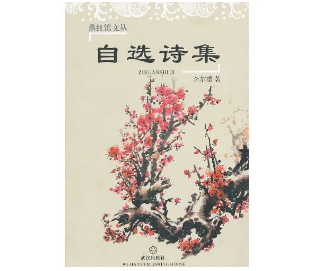
1914—1915年間,周作人幫助魯迅搜集、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該書輯錄了8種魏晉至隋朝學者所著會稽郡史傳、地記之佚書,目的在于“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于故”。受此啟發,周作人從1915年起,便有志于搜集越地鄉賢著作:“民國初年我在紹興城內做中學教師,忽發鄉曲之見,想搜集一點越人著作,這且以山陰會稽為限。”①據研究,周作人終其一生共收藏越地越人著作四百六十余部,這些著作大致可以劃分為四類:越地風土民俗的著作、越地歷史類著作、越人詩文集、其他越人著述。②
其中近三百部為越人詩文集,涉及詩、詞、文、日記、尺牘、詩話等文體。除王充、陸游之外,著者以明清時期為主,既包括王陽明、王畿、徐渭、屠隆、陶望齡、王思任、張岱、劉宗周、朱舜水、祁彪佳、胡天游、黃宗羲、章學誠、王衍梅、陶元藻、李慈銘、平步青等文史名家,也涵蓋了李壽朋、周調梅、魯曾熠、張桂臣、范嘯風、沈宸桂等名不見經傳的民間知識分子。當然,作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和批評家,周作人不止于搜集、收藏同鄉著作,還對之進行閱讀、理解、闡釋和傳承,且以一種特殊的“讀書錄”的方式寫成隨筆。
在這些隨筆中,他以閱讀為契機,大段摘抄原著,同時將自己的意見穿插其間。周作人就是以這種“夾抄夾敘”的方式來達成與諸位鄉賢之間的心靈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本文以周作人的這些“讀書錄”或曰“書話”為研究對象,試圖概括出他讀解鄉賢詩文的思想立場和基本觀點,這既有助于加深對周作人思想的理解,也有利于推進越地文學和文化研究。
一、“言志”:讀解鄉賢詩文的文學立場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正統文學觀念是“文以載道”,推崇“文治之文”,視文學為政教德化之業。周作人將此正統文學觀念命名為“載道”觀,而他自己則主張“言志”觀,他明確地提出:“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③他還經常襲用公安派的口號來表達“言志”觀,即“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這實際上屬于一種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學或文化立場(“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愿講的話”),也正是他讀解鄉賢詩文的基本立場。
在散文中,周作人非常推崇張岱和王思任,二人的特點在于講性靈、有個性、有趣味。周作人固然認為公安派和竟陵派將晚明性靈文學思潮推向了高峰,但是,在他眼中,張岱才是集大成者,“后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瑯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兩書,里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合后的大成績。”他尤其喜愛《陶庵夢憶》,原因在于:
一是“頗有趣味”;二是集中文章皆是“性情的流露”。④在《再談俳文》一文中,周作人指出,張岱為文難得有“俳諧”的情調,即使身處逆境,也常發調侃之語,這便與“載道”派的正經文章迥然有別。而在詼詭、戲謔的風格方面,王思任當然更具有典型性。周作人尤其欣賞他的《文飯小品》,他指出:“以詼諧手法寫文章,到謔庵的境界,的確是大成就,值得我輩的贊嘆”。總之,周作人認為,張岱和王思任都有反對名教的傾向,都能夠打破例規,“說自己的話”,從而與“載道”派拉開了距離。其文“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他們與徐渭一起,成為近三百年來浙江乃至中國文壇“飄逸”一派的代表性人物。⑤
周作人在《再談尺牘》一文中說:“我近來搜集一點尺牘,同時對于山陰會稽人的著作不問廢銅爛鐵也都想要,所以有些東西落在這交叉點里,叫我不能不要他,這便是越人的尺牘。”⑥他對尺牘和日記有所偏愛,因其更加便于“言志”,“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達作者的個性。”⑦茲舉一例。在明清時期的越人尺牘中,周作人除了閱讀過王畿、徐渭、陶望齡、王思任、張岱等名家之作,還專門抄錄了陶望齡的堂侄陶崇道的《拜環堂尺牘》。引起周作人注意的有兩點:
一者,陶崇道在書信中“亂談國事”,譬如,他曾寫道:“奴虜披猖,闌入內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將卒當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縉紳下及走卒,甘心剪發,女請為妾,子愿稱臣,牽挽不放胡騎北去者四越月于茲,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發之欲豎也。”⑧
這里既有對晚明軍政潰敗的揭露,言辭之中,也不乏對清軍的貶斥。但是,此書居然未被清朝列入禁書,這一點令周作人在滿足了一種“野史”癖之余,不免覺得驚奇。再者,陶崇道還時作“妙語”,如《通張葆一巡撫》中有一句:“弟處此譬之老女欲與群少年斗脂競粉,不特粗眉不堪細畫,亦覺宿酒不比新筜。高明何以教之?”周作人評論道:“這些文字都寫得不壞,自有一種風趣,卻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陳反新。”顯然,這是符合周作人的“言志”文學立場的。
二、“激發志氣”:對越中先賢的仰慕和評價
早在1915年,周作人在《讀書雜錄二十四則》中便輯錄了張岱的《於越三不朽圖贊》。此書記載了有明一代能夠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越中精英一百余人的圖贊,每人的圖贊均包含畫像、傳記、贊語三部分內容,寄托了張岱的仰慕之情、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周作人感嘆道:“后生小子,時一展對,足以激發志氣”。⑨在明朝文人中,周作人對徐渭和王思任極感興趣。圖贊中對徐渭描述道:“徐文長渭,山陰人。性縱誕不羈,以狂遭酈炎之獄,先文恭力救得出。出則放浪麴蘗,恣情山水,縱橫跌宕,益豪于詩”。王思任“少年狂放,以謔浪忤人,官不顯達,三仕令尹,乃遭三黜。”⑩
周作人對他們的“狂”追慕不已,在他看來,后世“專事苛細精干”的紹興“師爺”和“錢店官”與之相比,“那種豪放的氣象已全然消滅”。在越地先賢中,周作人自稱最佩服的是漢代王充。他在《藥味集•序》中說:“昔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來服膺此訓,以是于漢以后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則明李贄,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⑪
當清代李慈銘在《越中先賢祠目》中序例中提出:“然如王仲任為越士,首出《論衡》一書,千古談助,而其立言有違名教,故不與”,⑫試圖以“有違名教”的名義摒棄王充,這是周作人所不能茍同的。他認為,王充的疾虛妄的精神、愛真理的態度、重情理的文章才屬于真正的“儒家”。周作人將王充跟李贄、俞正燮一起列為中國思想界的三盞燈火,并對其《論衡》推崇備至:“王仲任為吾鄉先賢,素所景仰,嘗謂與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為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論衡》中九虛三增至今猶有萬丈光焰。”⑬
也正因為周作人將儒家精義縮減成“疾虛妄”“重情理”,所以對漢以后的儒家,尤其是程朱陸王之學頗為反感。他批評后世的儒家使重視人情物理的原始儒家走向了“道士化、禪和子化、差役化”,⑭淪落為虛偽的綱常名教。出于這種思想立場,他對越地先賢中的大儒總體評價并不高,譬如,對于張岱在《於越三不朽圖贊》中列為第一的王陽明,他很少提及。對劉宗周、黃宗羲等人也表示不感興趣。對于梁啟超所稱頌的“清初五大師”之一的鄉賢朱舜水,他倒是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但是,周作人在文中指出,“朱君的節義固極可欽,其學問則非我所能懂,蓋所宗無論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學總是不甚可解的。”他對朱舜水感興趣的主要有兩點:
第一,《朱氏談綺》中談到許多“果獻樹竹、禽鳥鱗介”等方面的生物學知識;第二,能體現出朱舜水個人性情的文字,“文集中的疏揭論議正經文字,又《陽九述略》,《安南供役紀事》等,固足以見其學問氣節,但是集里的書牘九卷,答問三卷,《談綺》三種,其瑣屑細微處乃更可見作者之為人,是很有意思的資料。”
不難看出,周作人對鄉賢的閱讀和理解是帶有鮮明的個人癖好的。三、“越人安越”:鄉賢詩作中的“事和景”周作人對紹興有濃厚的故鄉情結,這就是他在人到中年之后所謂的“越人安越”:“余生長越中,十八歲以后流浪在外,不常歸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跡不到浙江蓋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習性終于未能改變,努力說國語而仍是南音,無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無異于吃腌菜說享個時,愧非君子,亦還是越人安越而已。”⑮收集、閱讀越人的詩文集,正是滿足他思鄉之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于為什么喜歡看同鄉人的詩文,周作人有過明確的解釋,即出于“鄉曲之見”,“因為‘鄉曲之見’,所以搜集同鄉人的著作,在這著作里特別對于所記的事與景感到興趣,這也正由于鄉曲之見。
紀事寫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獨于鄉土著述中之事與景能隨喜賞識者,蓋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親歷,故感覺甚親切也。”⑯周作人搜集到很多同鄉人的詩作,如《會稽掇英集》《廣會稽風俗賦》《會稽三賦》《越中名勝賦》《越中百詠》《越詠》《鑒湖棹歌》《墟中十八圖詠》《越風》《娛園詩存》《柯園唱和集》《鞍存雜詠》《白華絳柎閣詩》《洗齋病學草》《越妓百詠》等等。但是,他關注的重點卻不是這些詩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而是其中所提到的家鄉的“事和景”。
為此,他曾自嘲道:“我這樣的讀詩文集,有人或者要笑為買櫝還珠,不免埋沒作者的苦心。”娛園是前清舉人秦樹銛的別業,李慈銘、陶方琦等著名文人所結的“皋社”就在那里。據周作人記載,他的大舅父是娛園主人的女婿,所以有了幾次游賞娛園的機會。
《娛園詩存》就是“皋社”詩人題詠娛園的詩詞集。如《娛園詩存》卷三中樊樊山的《望江南》一詞云:“冰觳凈,山里釣人居。花覆書床偎瘦鶴,波搖琴幌散文魚:水竹夜窗虛。”陶子縝的一首云:“澄潭瑩,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蠣洞,柳絲泉筑水鳧床:古幀寫秋光。”可以約略想見它的幽雅了。雖然周作人見到的娛園已然接近于廢墟,但作為兒童時代的游樂之地,留下的總是溫馨的回憶。更何況,在那里,周作人還有過一場“單相思”式的懵懂初戀,因此便對“娛園”有一種特別的情懷了。《柯園唱和集》是沈槱元、王袞錫等五十二人的唱和之作,收錄七言絕句五百八十首。
周作人說:“鄙人不解詩,讀之亦覺得無甚好句,但是對于此集感到興趣者,則以柯園乃是沈園故址故也。”沈園因陸游和唐婉的愛情悲劇而聲名遠揚,周作人便又聯想到著名詩人陸游,他引用《越風》中的一段記載:“沈翁家有園亭,在春波橋畔,放翁逢其故婦詩,曾見驚鴻照影來,即此地也。少時觴詠其下,有和主人柯園諸景詩。內一方池澄泓,可鑒毫發。”對于周作人而言,沈園既是一種文化記憶,也是一抹文化鄉愁。
他曾賦詩一首:“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另外,在讀詩集《繞竹山房詩稿》時,周作人也表示:“詩不甚懂得,《續稿》中有絕句數十首紀鄉土風物,頗覺可喜。”很多時候,他甚至將這些詩集作為越地民俗的資料,這確實是周作人讀詩的獨特之處。
四、結語:周作人闡釋鄉賢詩文之失
綜上所述,周作人收藏并閱讀了近三百部越人詩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學立場和疾虛妄、重情理的“儒家人文主義”思想角度,他對鄉賢著作的閱讀和闡釋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他對那些能夠獨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別感興趣,對尊重科學常識,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別關注,對鄉賢詩文中提及的故鄉景物無不為之動容。但是,周作人對先賢著作的閱讀和接受并非沒有問題。
首先,他的“言志”文藝觀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理念的,“至少在理論上徹底放棄了對于國家、民族、社會、人民的任何宗教性的信仰和責任感,還原為純粹的個體,把五四時期已經提出的‘救出你自己’的個人本位主義原則發展到極端。”⑰以這種眼光去讀詩文,必然會出現偏差。譬如,對于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周作人居然無視他的九千多首愛國詩作,僅對《老學庵筆記》感興趣,而且也只是關注其中的“瑣語”,甚至說:“《筆記》中有最有意義也最為人所知的一則,即關于李和兒的炒栗子的事。”其實,《老學庵筆記》同樣滲透著陸游的愛國主義精神,周作人的這種解讀完全是避重就輕,難免會誤導讀者。
其次,周作人將儒家思想縮減為“疾虛妄、重情理”,將程朱陸王之學一概視為綱常名教而加以批判,也是有偏頗的。簡要地說,儒家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實現“仁政”理想的,同時,也有利于提升民眾的道德修養。越中第一大哲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的精義也正在于此。然而,周作人對此是麻木的,這在一個側面上也體現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批判儒家思想的偏差。
作者:丁文敬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和影響
- 2025-02-10經管專業快速發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據庫?scopus數據
- 2025-01-24scopus發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表的論文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