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除權(quán)判決與公示催告制度的完善
時間:2019年07月29日 分類:政法論文 次數(shù):
摘要:基于票據(jù)的設權(quán)性與無因性之統(tǒng)一,其內(nèi)囊括之實體權(quán)利與其外存在之承載介質(zhì)本在一般條件下密不可分,對介質(zhì)客體的背書占有是行使票據(jù)內(nèi)在權(quán)利之充要條件。但當票據(jù)介質(zhì)未處于實際最后權(quán)利人占有的狀態(tài),其不僅存在被第三人取得并繼續(xù)流通的可能,亦會進一步導致實際最后權(quán)利人合法利益受損。
因此,在進行除權(quán)判決時,如何保護實際最后權(quán)利人的利益行使,防止惡意申請公示催告的救濟途徑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票據(jù)被惡意除權(quán)后實際最后合法持票人如何實現(xiàn)救濟為爭議焦點的一個典型案例進行切入,分析目前我國票據(jù)除權(quán)判決與公示催告制度存在的問題,并對票據(jù)除權(quán)之訴的系統(tǒng)立法完善及司法適用提出合理建議。
關鍵詞:失票救濟;票據(jù)除權(quán)之訴;惡意公示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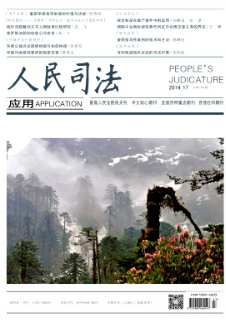
一、公示催告制度完善之正當性分析
(一)公示催告制度完善的理論價值
從關鍵詞視角看,我國學界分別圍繞“除權(quán)判決的法律效力”與“除權(quán)判決的救濟制度”的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時日,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國學界對此制度建構(gòu)與完善的認知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20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國內(nèi)學者開始涉獵,但是到21世紀初才逐漸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并成為經(jīng)濟學和法學等學科的研究課題。
首先,對金融意義上的票據(jù)以及票據(jù)開支、承轉(zhuǎn)、規(guī)范使用的研究最早來自經(jīng)濟學界,他們從2003年左右開始較為系統(tǒng)地對票據(jù)進行理論研究,并主要從一般概念上探討票據(jù)的發(fā)展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的辯證關系、票據(jù)的開具、使用、作廢流程以及國外票據(jù)支付結(jié)算等情況,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金融創(chuàng)新:中國票據(jù)市場有序發(fā)展的必由路徑》(2003,闕方平、朱華)、《我國票據(jù)市場發(fā)育的制度性障礙及其變遷路徑的選擇》(2000,盧新波)、《論適度開放融資票據(jù)》(2002,秦池江)、《我國票據(jù)市場風險的表現(xiàn)與外部環(huán)境的優(yōu)化》(2002,王雅茜等)、《論票據(jù)抗辯》(王海英,2003)、《制度非均衡下的票據(jù)激勵:金融信用資源配置權(quán)的三重博弈》(2004,王馨)、《淺析我國票據(jù)制度的理論基礎選擇問題》(2005,孔繁強)等。
到了2009年左右,一些經(jīng)濟學、管理學者開始從微觀層面關注具體的票據(jù)流程規(guī)范和風險管理,以及票據(jù)貼現(xiàn)利率浮動方式,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票據(jù)理財產(chǎn)品的銀信合作模式、市場概況與政策思考》(2009,汪辦興)、《商業(yè)銀行票據(jù)業(yè)務事業(yè)部制改革研究》(2009,陳江偉)、《票據(jù)創(chuàng)新:融資性票據(jù)引入及制度構(gòu)建》(2009,劉英)、《中期票據(jù)市場回顧及發(fā)行利率實證分析》(2010,陳芳)、《商業(yè)銀行票據(jù)貼現(xiàn)利率的市場化轉(zhuǎn)型———以Shibor為基準的定價模型研究》(2010,汪辦興)等。
從2011年左右開始,一些學者開始集中關注票據(jù)遺失的救濟方式,并在票據(jù)救濟的比較研究和制度構(gòu)建方面形成了一批成果,如《論票據(jù)喪失后的掛失止付》(2011,柯昌輝)、《經(jīng)濟學視角下我國票據(jù)權(quán)利喪失立法之完善》(2011,劉道云)、《我國票據(jù)市場發(fā)展創(chuàng)新思路探討》(2012,趙邦洪等)、《淺析我國票據(jù)市場的現(xiàn)狀及完善措施》(2012,肖小和)、《聲譽機制、信用評級與中期票據(jù)融資成本》(2013,王雄元)、《日本空白票據(jù)規(guī)則及對我國的啟示》(2015,王艷梅)等。
就法學界而言,我國法學學者從2008年左右開始較為系統(tǒng)地對票據(jù)遺失的救濟問題進行理論研究,并集中于從一般意義上研究票據(jù)與金融穩(wěn)定的關系、票據(jù)法律規(guī)范體系構(gòu)建以及國外票據(jù)法律規(guī)范設定等命題,形成了一定的成果,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我國票據(jù)法中無對價抗辯制度的完善》(2008,李偉群)、《關于票據(jù)法律確立融資性票據(jù)制度的對策探究》(2008,王林等)、《設質(zhì)背書的效力研究兼及票據(jù)法與物權(quán)法的沖突及其解決》(2009,高勝平)等。
到了2014年左右,相關研究主要從票據(jù)除權(quán)制度深入設計、立法價值取舍、救濟制度構(gòu)建、除權(quán)后保障以及與侵權(quán)之訴關系等方面展開深入分析,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論票據(jù)公示催告程序的制度完善》(2014,楊忠善)、《票據(jù)法修改中立法理念的選擇》(2014,王峙焯)、《關于票據(jù)公示催告與除權(quán)救濟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研究》(2014,何方)、《論票據(jù)利益返還請求權(quán)制度的廢除》(2015,徐曉)等。
還有一些文章立足于分析國外相關制度的可供借鑒之處,如《中美票據(jù)市場發(fā)展中的風險比較》(2015,朱曉曉)、《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流通票據(jù)編評析》(2015,吳興光)等。以上研究成果盡管對案例分析研究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均沒有置于“防止惡意除權(quán)”的語境下展開,更沒有專門涉及完善公示催告程序的法律配置問題,而僅僅于文章中有所提及。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學術(shù)界關于該論題的研究尚處于初始狀態(tài)。因此,有必要對該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二)公示催告制度完善的現(xiàn)實意義
票據(jù)的產(chǎn)生與存續(xù)源于其流通性與便利性,在經(jīng)濟活動中,票據(jù)可以實現(xiàn)頻繁的流通轉(zhuǎn)讓,有利于商品交易和資金融通,但是另一方面,過度的便利性也會導致流通中的票據(jù)因被盜、遺失或滅失等原因而致使權(quán)利人的票據(jù)權(quán)利不能得到順利實現(xiàn),甚至受到惡意侵害。因此,法律為票據(jù)權(quán)利人設計出一種救濟制度,允許因各種原因失去票據(jù)的權(quán)利人向法院提出申請,法院根據(jù)公示催告申請人的申請,以公示方式在一定時間內(nèi)通知利害關系人。當“在公示催告期間屆滿而無人申報權(quán)利,或者有人申報權(quán)利但被法院駁回時,作出宣告票據(jù)無效的判決[1]”。
這種判決在民事訴訟理論上稱為除權(quán)判決。它是對票據(jù)權(quán)利人進行救濟的重要途徑,也是申請人申請公示催告的主要目的。但是,正如“票據(jù)喪失后,存在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并進一步流通的可能。公示催告程序僅有一方當事人,且法院進行形式審查,即使申請人偽報失票,惡意申請公示催告,也很難被發(fā)現(xiàn)。[2]”在進行除權(quán)判決時,由于缺乏較為完善的審查與篩選制度,惡意申請公示催告的比例較高。因此,如何防止惡意申請,從而保護合法持票人的票據(jù)權(quán)利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票據(jù)除權(quán)之訴作為保障利害相關人權(quán)益中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除權(quán)后的票據(jù)權(quán)利救濟,需要進行進一步立法完善以及司法改進。以票據(jù)除權(quán)訴訟典型案例進行切入,通過案例分析的形式從案例中透析出目前我國票據(jù)除權(quán)之訴中公示催告程序在司法運行中的現(xiàn)狀,是反應該制度運行缺陷,為該制度優(yōu)化升級提供切實可行性建議的有效分析方式。
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下稱《民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jù)法》[3](下稱《票據(jù)法》)《票據(jù)管理實施辦法》[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3](下稱《規(guī)定》)《支付結(jié)算辦法》[3]等法律與司法解釋中相關條款,探析主要包括票據(jù)最后合法持有人的認定標準,惡意申請公示催告程序的認定標準,票據(jù)經(jīng)惡意公示催告申請被除權(quán)后應提起訴訟的性質(zhì)等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的一系列相關問題。
這需要立足于完善除權(quán)判決法律制度這一核心概念,全面檢視現(xiàn)有立法模式與機制的利弊得失,推進有關理念更新與制度變革,以期提升國家金融領域治理能力,實現(xiàn)治理現(xiàn)代化。這更有助于降低監(jiān)管成本和提高監(jiān)管水準、有助于保護最后合法持票人與票據(jù)利害關系人切身利益、有助于推動司法實踐標準統(tǒng)一,也有助于為遭受惡意除權(quán)的合法持票人提供更多的救濟路徑選擇,從而進一步保護真正的合法持票人行使實際票據(jù)權(quán)利。
二、典型案例簡介
(一)典型案例———常州市崢妍紡織品有限公司訴淮安市淮安特鋼有限公司票據(jù)糾紛案
1.案情概述
2009年淮安市淮安特鋼有限公司(下稱淮安公司)以銀行承兌匯票遺失為由向江蘇省淮安市清河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申請,公示期間無人申報權(quán)利,法院依法作出除權(quán)判決,宣告原票據(jù)權(quán)利無效。將票據(jù)權(quán)利給予淮安公司,在判決生效后淮安公司即刻將票據(jù)提現(xiàn)。后原告常州市崢妍紡織品公司(下稱崢妍公司)在知悉后以淮安公司提起惡意公示催告,侵害自身實際票據(jù)權(quán)利為由,要求返還包含本金和利息在內(nèi)的票據(jù)利益。
經(jīng)查明,該匯票系惡意第三人周某某騙取。崢妍公司訴由要點在于,其是票據(jù)連續(xù)背書標注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其持有的票據(jù)由淮安公司作為支付憑證后,未實際取得占有。而在交易結(jié)束后,淮安公司在未通知崢妍公司的情況下將該匯票交給了第三人周某某后,在背書人一欄加蓋了公章。但是由于其并未在被背書人部分取得簽章,因此不能認為是連續(xù)背書,該背書行為無效。
2.審判要點
一審法院審判要點有三:首先,連續(xù)背書是除無記名票據(jù)與空白背書票據(jù)外合法持票人證明其匯票權(quán)利的唯一方式。除此之外的其他享有票據(jù)實際權(quán)利的情況需要通過合理舉證進行證明。而淮安公司提供的相應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其通過基礎關系取得票據(jù)之事實。其次,基于票據(jù)的文義性,持票人在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時,僅能以記載于票據(jù)上的文義內(nèi)容加以實施,而排除在票據(jù)記載范圍之外的證據(jù)。因此淮安公司提供的相關交易憑證不應作為本案證據(jù)。
再次,由于淮安公司與第三人周某某不存在基礎關系,且其在轉(zhuǎn)交匯票的過程中沒有進行連續(xù)背書,因此即使淮安公司確實是失票人,但不能被認定為最后的合法持票人,票據(jù)一經(jīng)轉(zhuǎn)移,淮安公司即失去票據(jù)權(quán)利,后來的除權(quán)判決,并不是在事實上承認淮安公司為合法持票人,而只是使其擁有失票人的訴權(quán)。綜上幾點,對崢妍公司的訴訟請求應予以支持,淮安公司的抗辯理由予以駁回。
(二)案件爭議焦點本案的爭議焦點較多,特別是一審法院與二審法院的判決依據(jù)有較大的差異,因此選為典型案例進行研究可以較深入地體現(xiàn)目前公示催告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爭議大概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原告與被告的合法持票人身份認定標準。包括經(jīng)過買賣方式取得但沒有背書的票據(jù)是否具有效力,這種情況是否屬于《票據(jù)法》第31條“其他方式取得票據(jù)”的情形。第二,被告由于票據(jù)被騙取而申請公示催告程序的行為是否屬于惡意申請。第三,若票據(jù)在被惡意除權(quán)后,最后合法持票人所提起的訴訟性質(zhì)是在程序法公示催告程序基礎之上產(chǎn)生的撤銷之訴,還是在民法的侵權(quán)損害之上提出的侵權(quán)損害賠償之訴。
具體來說:1.原告與被告是否為最后合法持票人本案中訴訟雙方均以其為該匯票的最后合法持票人為由進行抗辯,崢妍公司認為其是匯票所記載的最后背書人,因此應是最后合法持票人。而淮安公司以其實際占有的匯票被惡意第三人騙取,以及經(jīng)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除權(quán)判決產(chǎn)生的“既判力”為由進行抗辯。一審法院與二審法院雖然都對原告合法持票人的地位進行了確認,但是關于其是否享有票據(jù)權(quán)利卻產(chǎn)生了分歧。
一審法院以票據(jù)法定主義出發(fā)認定淮安公司在未背書的情況下取得票據(jù),不應認為是最后合法持票人,經(jīng)過除權(quán)判決之后,崢妍公司喪失了其票據(jù)權(quán)利,也不再享有繼續(xù)在匯票上記載并且背書的權(quán)利,但仍應當認定為在除權(quán)判決生效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二審法院基于受讓人從無票據(jù)處分權(quán)人手中取得票據(jù)、依照票據(jù)法規(guī)定的轉(zhuǎn)讓方式取得票據(jù)、取得票據(jù)時無惡意或者重大過失三個要件[4]確定崢妍公司最后合法持票人的身份,因此認定其未喪失實際的票據(jù)權(quán)利。而淮安公司在明知其行為會損害實際票據(jù)權(quán)利的情況下,通過惡意申請公示催告并成功除權(quán),最后貼現(xiàn)匯票權(quán)利,具有侵害票據(jù)合法持有人實際權(quán)益的事實,因此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兩級法院雖然都認定崢妍公司是合法的最后持票人,但是其法律依據(jù)卻是不同的。
2.被告申請公示催告程序行為的性質(zhì)
在法庭調(diào)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本案中淮安公司在一開始是以保管不慎造成票據(jù)丟失為由申請公示催告程序的,而在案中的惡意第三人周某某被捕后,淮安公司才稱票據(jù)由于被騙取而遺失,并且提供了交易相關單據(jù)與憑證。后淮安公司以票據(jù)被騙取為由,辯稱由于喪失票據(jù)而申請公示催告程序的行為并不是基于惡意。稱“以遺失為名的公示催告程序?qū)賽阂鈷焓菍Α睹袷略V訟法》相關條款的曲解。”
確實,雖然《規(guī)定》第24條有“票據(jù)喪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的相關規(guī)定,但是《民事訴訟法》第281條同樣存在“因票據(jù)被盜、遺失或者滅失”以及“可以申請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項”的幾種條件下,其中包括可以背書轉(zhuǎn)讓的票據(jù)持有人可以向票據(jù)支付地的基層人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程序的相關規(guī)定,而淮安公司明顯不符合該條件。由此可以看出,相關司法解釋與法律存在一定的矛盾,還需要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以列舉式明確惡意申請的認定標準。
3.原告提起的訴訟類型是否適當
本案中崢妍公司以惡意申請除權(quán)判決侵害自身票據(jù)利益為由起訴被告淮安公司。被告淮安公司則以除權(quán)判決具有既判力,原告應重新起訴為由進行抗辯。本案中一審二審法院均駁回了被告的抗辯事由,然而法院處理的依據(jù)卻不相同。一審法院認為“除權(quán)判決并非創(chuàng)設新的票據(jù)權(quán)利,而是對權(quán)利的重新確認,因而除權(quán)判決所確認的票據(jù)權(quán)利內(nèi)容應與被宣告無效的票據(jù)權(quán)利相一致,不能優(yōu)于原票據(jù)上記載的權(quán)利。”認定被告行為客觀上造成了原告票據(jù)權(quán)利不得實現(xiàn)的損害現(xiàn)實,支持原告提起由惡意申請造成的侵害票據(jù)權(quán)益的賠償訴求。
二審法院認為雖然原告已經(jīng)喪失了實際票據(jù)權(quán)利,但是原告滿足票據(jù)取得三要件,加之被告基于故意虛構(gòu)事實來進行惡意除權(quán),并且實際產(chǎn)生了損害后果,行為與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此支持原告訴求,駁回被告辯由。兩級法院雖然都支持崢妍公司的賠償訴求,但是一審法院是基于除權(quán)判決雖有既判力,卻由于被惡意申請而啟動,因此不能對抗普通訴訟程序為出發(fā)點,是從程序法角度進行的支持。而二審法院是從認定被告的惡意申請行為符合侵權(quán)三要件構(gòu)成侵權(quán)因此需負賠償責任,是從實體法角度進行的支持。兩級法院在審判時的出發(fā)點有很大的不同。
三、關于案件爭議焦點的法律分析
(一)關于票據(jù)的最后合法持票人認定標準
《票據(jù)法》(1996年制定,2004年修改)第30條:“匯票以背書轉(zhuǎn)讓或者以背書將一定的匯票權(quán)利授予他人行使時,必須記載被背書人名稱。”第31條第一款:“以背書轉(zhuǎn)讓的匯票,背書應當連續(xù)。持票人以背書的連續(xù),證明其匯票權(quán)利;非經(jīng)背書轉(zhuǎn)讓,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匯票的,依法舉證,證明其匯票權(quán)利。”除此之外,《票據(jù)法》第12條第一款有“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jù)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jù)的,不得享有票據(jù)權(quán)利”的規(guī)定。根據(jù)案情,淮安公司在轉(zhuǎn)讓該票據(jù)之時并沒有合法有效的背書,因此,原告為最后合法持票人,享有票據(jù)權(quán)利。
一審法院是以結(jié)合我國《票據(jù)法》第31條的票據(jù)法定主義為出發(fā)點確定原告雖然喪失票據(jù)文義權(quán)利,卻仍然擁有票據(jù)的實際權(quán)利。二審法院主要是依據(jù)票據(jù)權(quán)利取得三要件,結(jié)合票據(jù)法第10條、第12條、第31條的相關規(guī)定,認定原告具有所持票據(jù)形式合法、取得票據(jù)手段合法、取得票據(jù)時主觀善意的三要件,判斷原告具備票據(jù)的真正合法持有人的條件,也就享有票據(jù)實際權(quán)利。在駁回被告抗辯事由時,一審法院同樣以票據(jù)法定主義回應,依據(jù)《票據(jù)法》第14條、第31條確定被告不具有合法持票條件。二審法院則依據(jù)《票據(jù)法》第4條第一款“票據(jù)出票人制作票據(jù),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jù)上簽章,并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jù)責任。”結(jié)合第31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即“票據(jù)上的文義記載不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與實際情況不符,也不得用票據(jù)之外的證據(jù)變更或補充票據(jù)上的記載內(nèi)容[5]。”因此,被告以匯票被欺詐為由進行抗辯是不成立的。
(二)票據(jù)經(jīng)惡意公示催告申請被除權(quán)后應提起訴訟的性質(zhì)《民訴法》(1994年制定,2007、2012、2017年修訂)單設第十八章規(guī)定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公示催告程序,其中第218條第二款有“申請人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申請書,寫明票面金額、發(fā)票人、持票人、背書人等票據(jù)主要內(nèi)容和申請的理由、事實”的內(nèi)容。第219、220條規(guī)定了停止支付的期限、第221、222條規(guī)定了利害關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間未申報權(quán)利,票據(jù)權(quán)利與實體相分離、第223條規(guī)定除權(quán)后的訴訟救濟制度(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很少使用)。
除此之外,《民訴法》第218條規(guī)定“能夠適用公示催告程序的票據(jù),被申請除權(quán)的票據(jù)需是持有人被盜、遺失或滅失的票據(jù)”;《民事訴訟法解釋》(2015年制定)第226條、《規(guī)定》第26條有:“可以申請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規(guī)定可以背書轉(zhuǎn)讓的票據(jù)在喪失票據(jù)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四、我國票據(jù)除權(quán)判決法律制度問題分析
目前,我國法院對公示催告申請資格僅進行形式審查,其本意是讓盡量多的當事人參與到公示催告程序中,從而防止第三人取得并進一步流通。但是,公示催告程序僅有一方當事人,加之現(xiàn)有通知公示催告手段落后,至于合法持票人往往在貼現(xiàn)時才知道票據(jù)已被除權(quán)。結(jié)合現(xiàn)在較高的惡意申報率與不完善的國家電子票據(jù)系統(tǒng),公示催告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的缺陷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偏離其設計本意。
五、完善我國票據(jù)除權(quán)判決法律制度問題的對策建議
公示催告程序的制度缺陷,集中體現(xiàn)在除權(quán)之訴中申請主體資格標準模糊、公示催告程序?qū)е聬阂馍陥蟊壤呔硬幌隆﹃P系人缺乏衡量標準與范圍等,導致合法持票人的票據(jù)權(quán)利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因此,應當盡快完善立法,統(tǒng)一規(guī)范目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同操作標準,從而完善我國票據(jù)法律體系。
六、結(jié)語
在實踐中由公示催告程序與除權(quán)判決產(chǎn)生的程序性問題與實體法理論存在較大差異。加之《票據(jù)法》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導致在失票救濟問題上合法持票人權(quán)利無法得到較好保護。《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沒有對提起申請公示催告的準入條件以及相應罰則做出規(guī)定,同時對“利害相關人”“失票申請人”的概念也模糊不清。《票據(jù)糾紛規(guī)定》包含的失票救濟性質(zhì)亦需進一步明確。因此,有必要在立法與司法層面通過明確票據(jù)除權(quán)判決申請人范圍與標準、進一步完善公示催告程序、建立惡意申請篩選制度等方式,完善我國的票據(jù)除權(quán)判決法律制度,保護合法持票人的切身利益。
[參考文獻]
[1]邢海寶.票據(jù)公示催告的限縮與轉(zhuǎn)向[J].法學,2018(5):108-117.
[2]傅鼎生.我國票據(jù)制度未賦予交付轉(zhuǎn)讓的效力[J].法學,2009(12):110-120.
[3]北大法寶網(wǎng).法律法規(guī)檢索[DB/OL].[2018-01-15].
[4]曲昇霞,袁江華.票據(jù)公示催告程序適用條件之分析[J].人民司法,2014(21):92-97.
[5]張雪楳.票據(jù)喪失救濟之公示催告程序疑難問題研究———兼論票據(jù)權(quán)利人的認定[J].人民司法,2015(8):16-25.
相關刊物推薦:《人民司法》系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刊,1957年1月由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主要奠基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長董必武同志倡議創(chuàng)辦并題寫刊名。
SCI期刊目錄
SCI論文
- 2025-04-03Current Science期刊投稿須知
- 2025-04-03回復SCI審稿人的策略及回復信的
- 2025-04-02Journal of Blood Medicine醫(yī)學4
SSCI論文
- 2025-02-28新聞傳播研究專業(yè)英文論文可選的
- 2025-02-19Cogent Education期刊分區(qū)和影響
- 2025-02-10經(jīng)管專業(yè)快速發(fā)表ssci論文的做法
EI論文
- 2025-04-02見刊快檢索快的EI會議推薦和匹配
- 2025-03-05EI會議在哪發(fā)論文,解答及指導
- 2025-03-01EI會議論文值得發(fā)嗎?2025EI會議
SCOPUS
- 2025-02-07什么是全文型數(shù)據(jù)庫?scopus數(shù)據(jù)
- 2025-01-24scopus發(fā)表文章格式修改指南
- 2024-11-19Scopus收錄的建筑工程類期刊
翻譯潤色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應該用什么
- 2024-11-22國際中文教師能在國際中文期刊發(fā)
- 2024-11-22國際中文期刊評職稱承認嗎
期刊知識
- 2025-04-01復合材料科學與工程論文投稿word
- 2025-04-01安全教育論文推薦適合投的不同級
- 2025-03-2915本教育類雙核心期刊!門檻低,
發(fā)表指導
- 2025-03-31精選交通節(jié)能領域論文選題31個,
- 2025-03-28電子技術(shù)與智能家具可參考文獻37
- 2025-03-25電催化析氫方向新發(fā)表的論文文獻